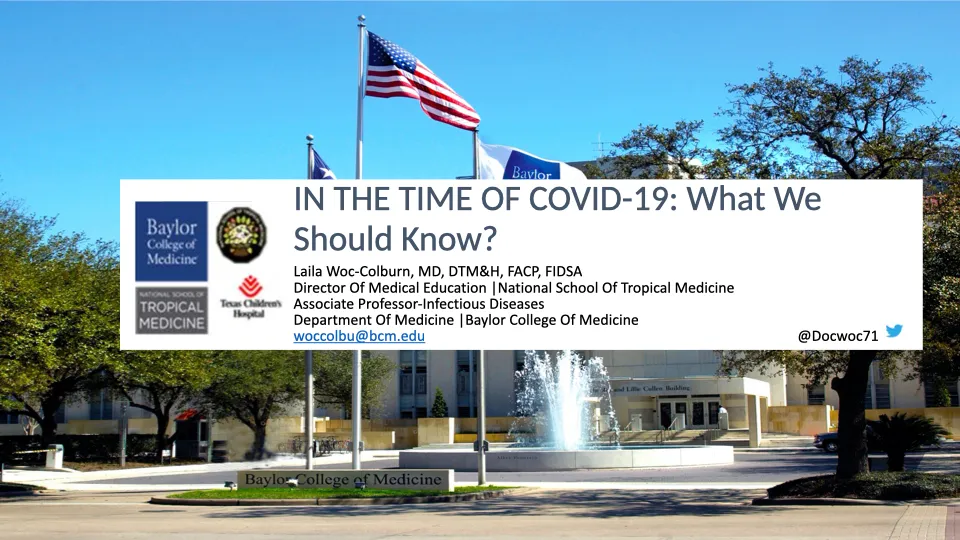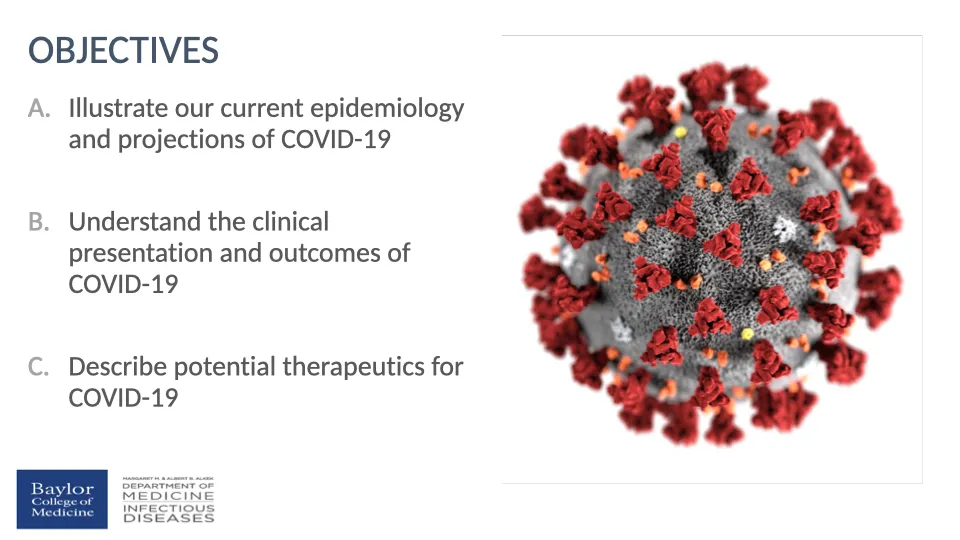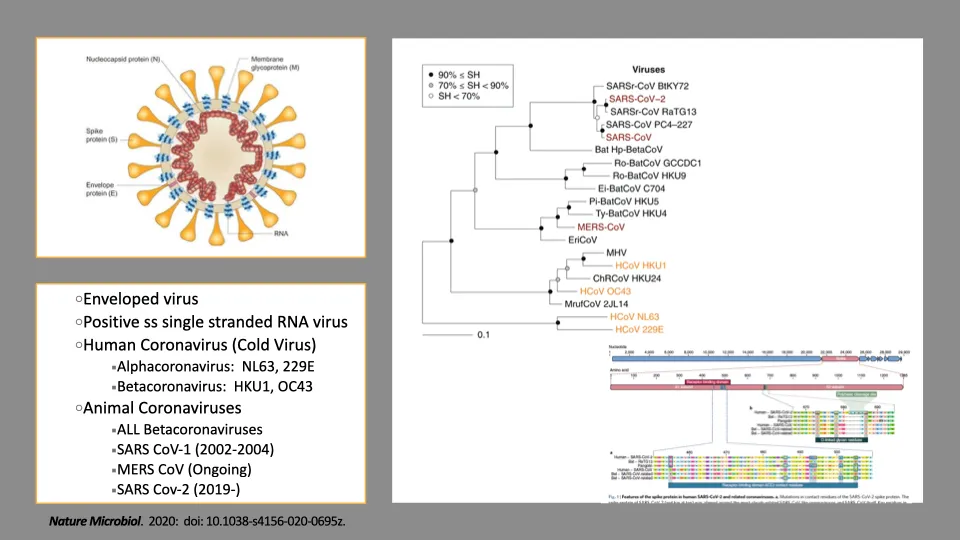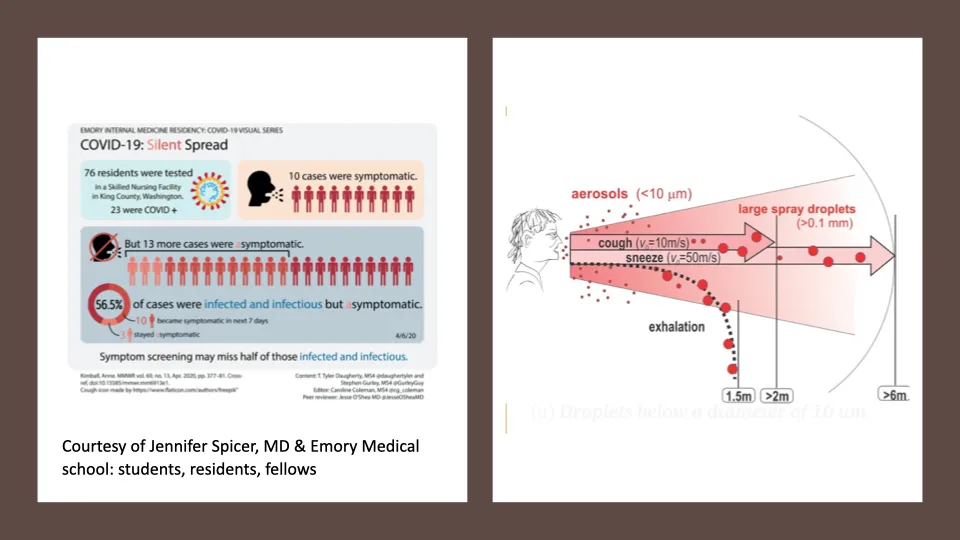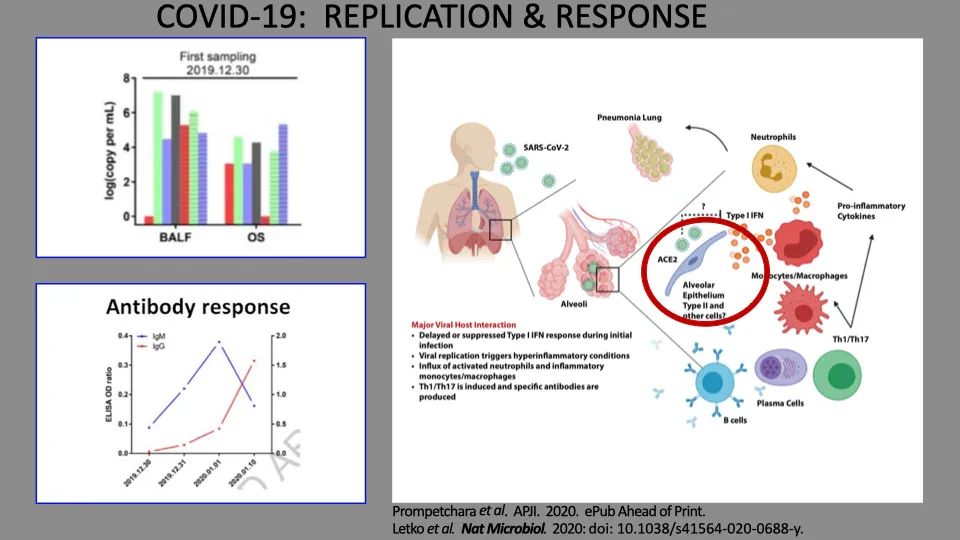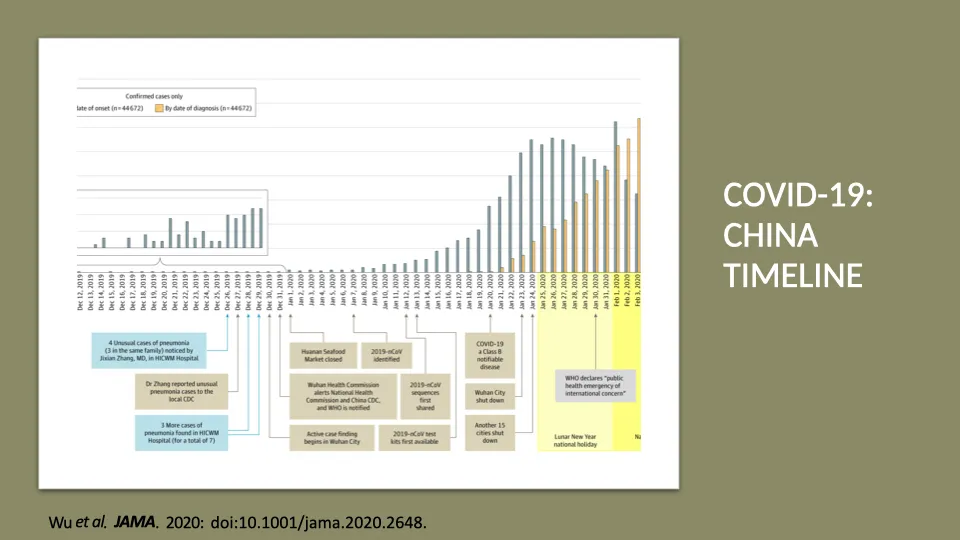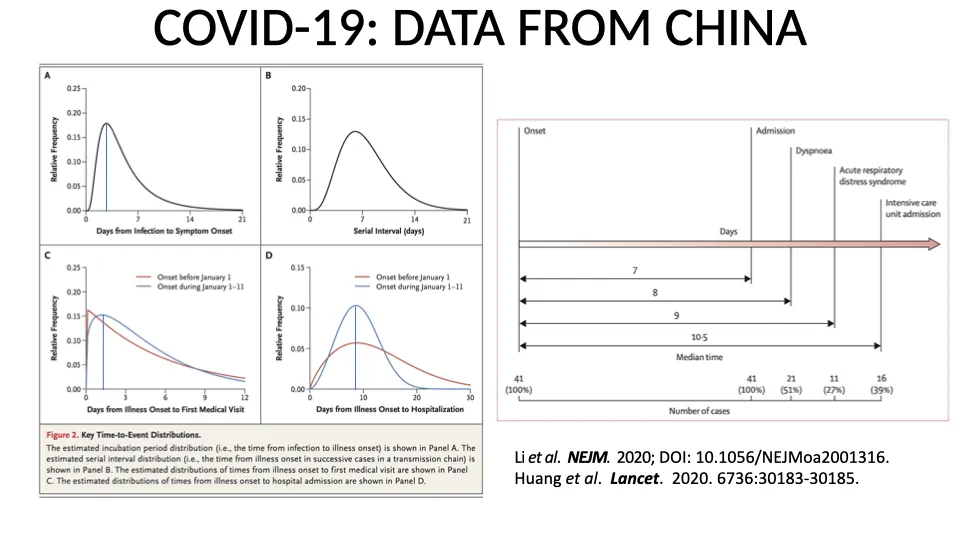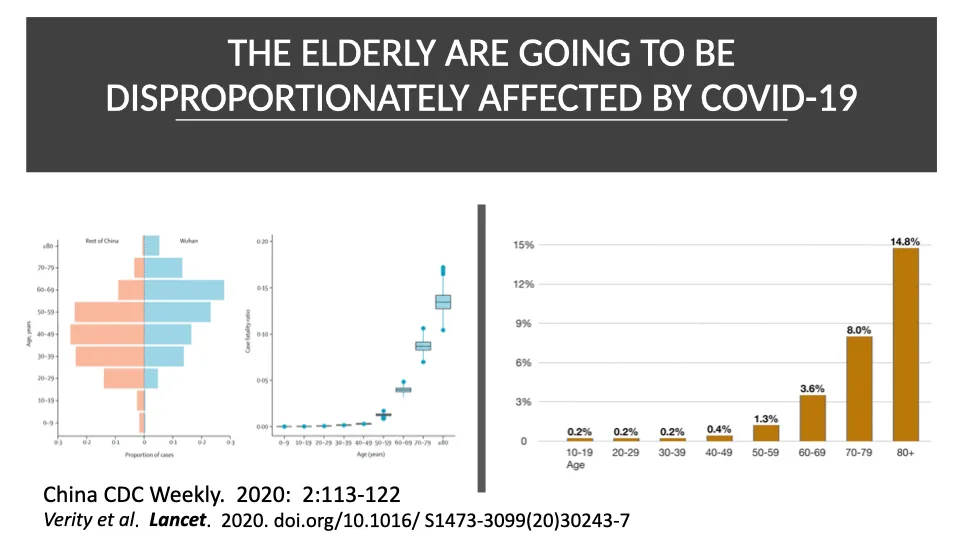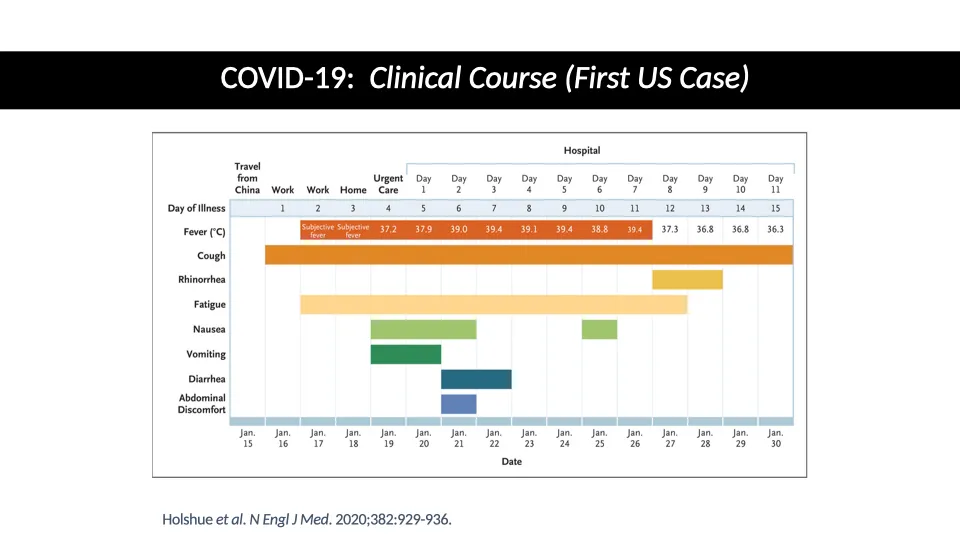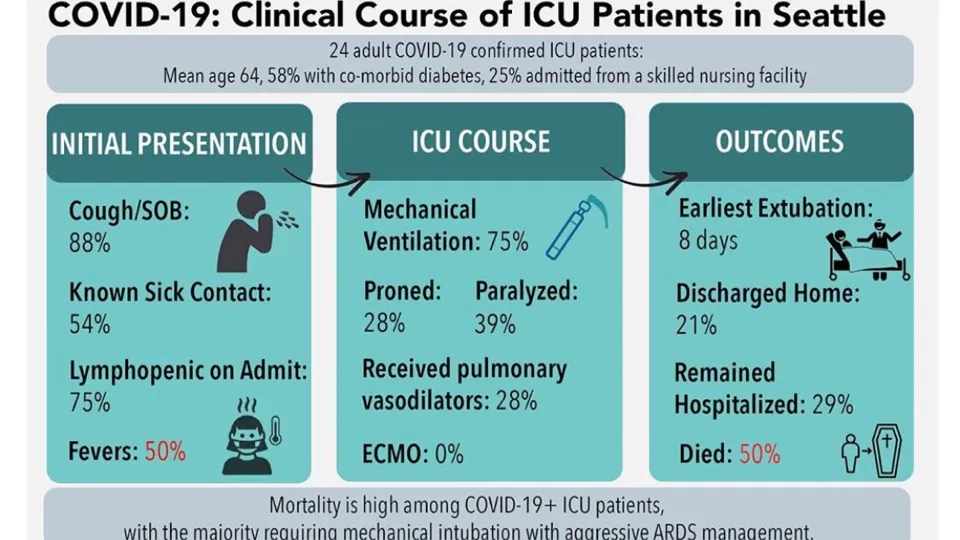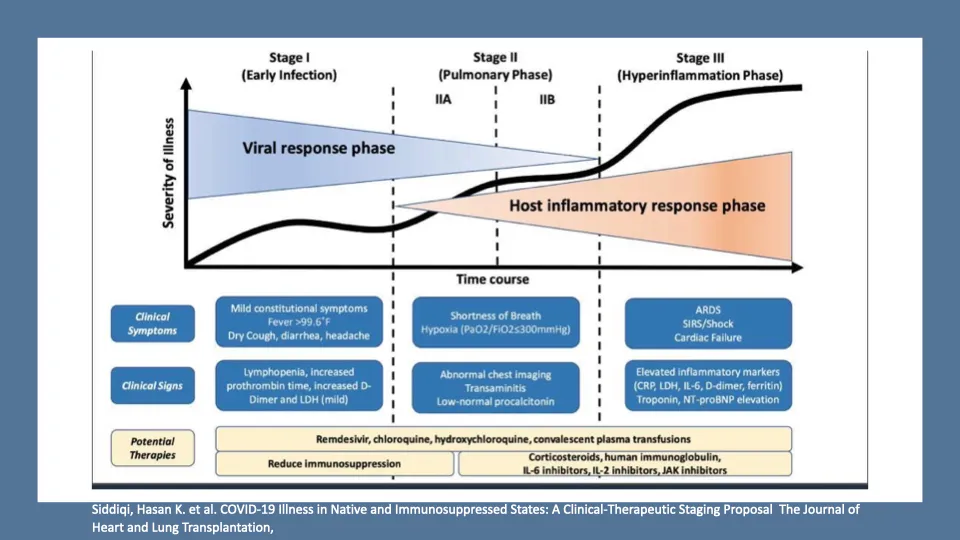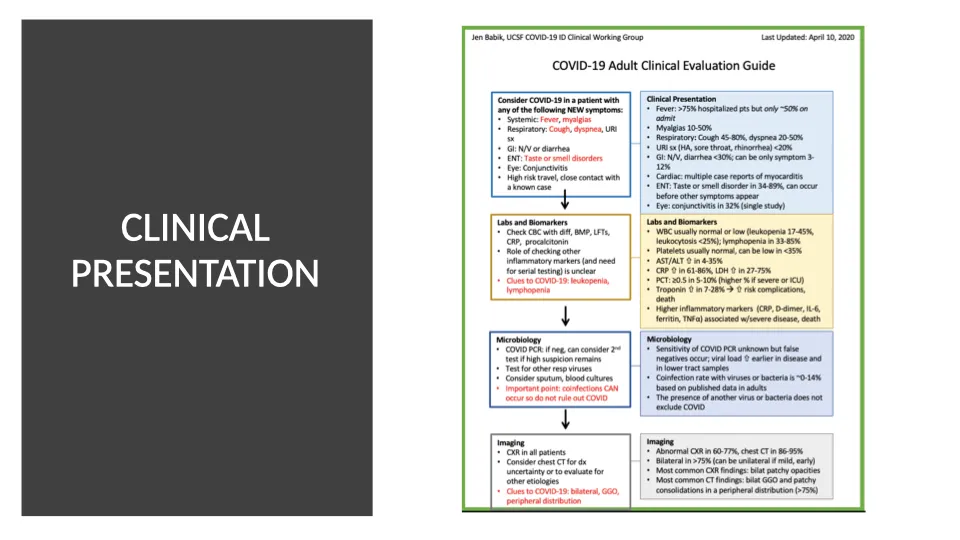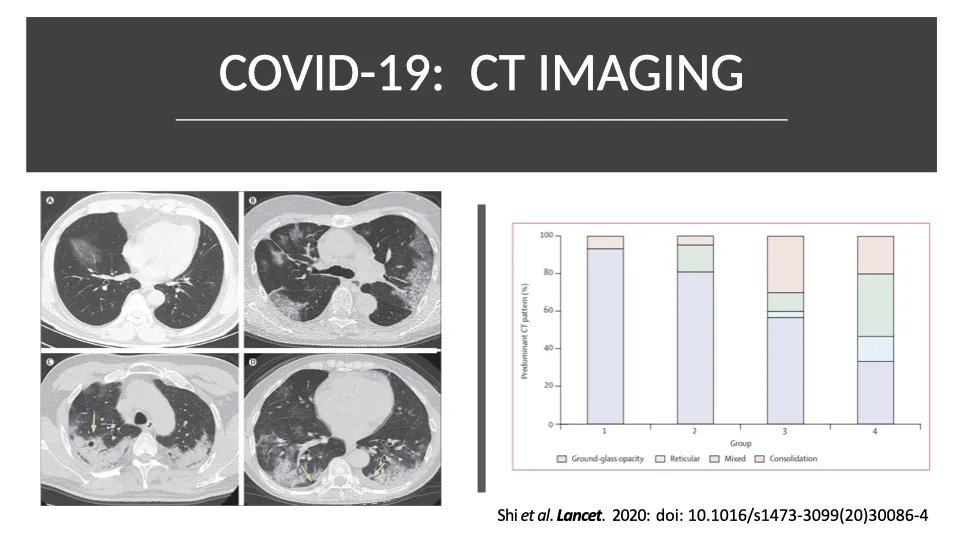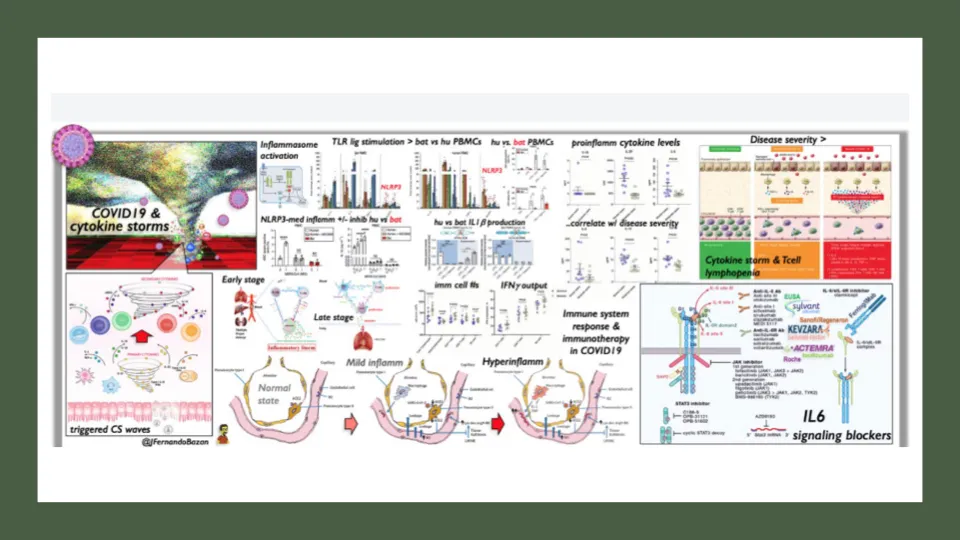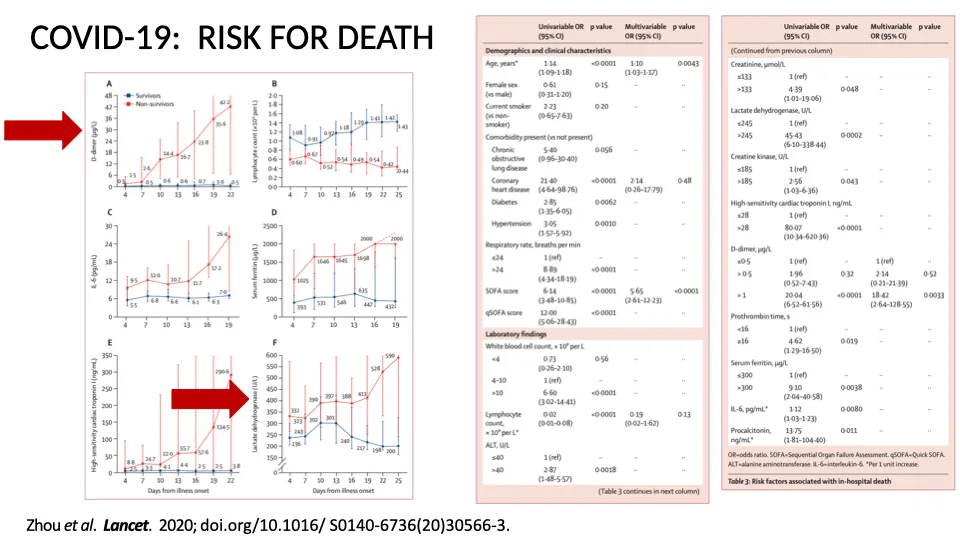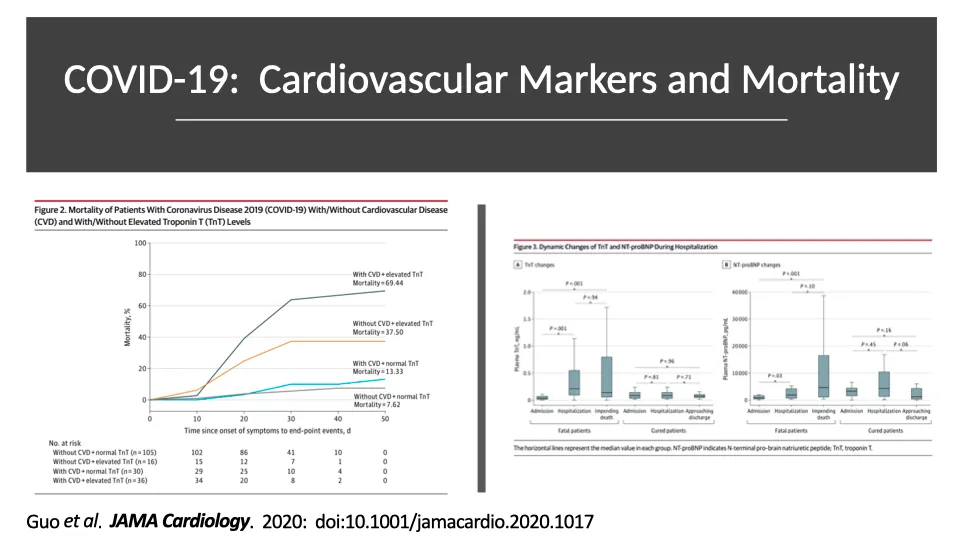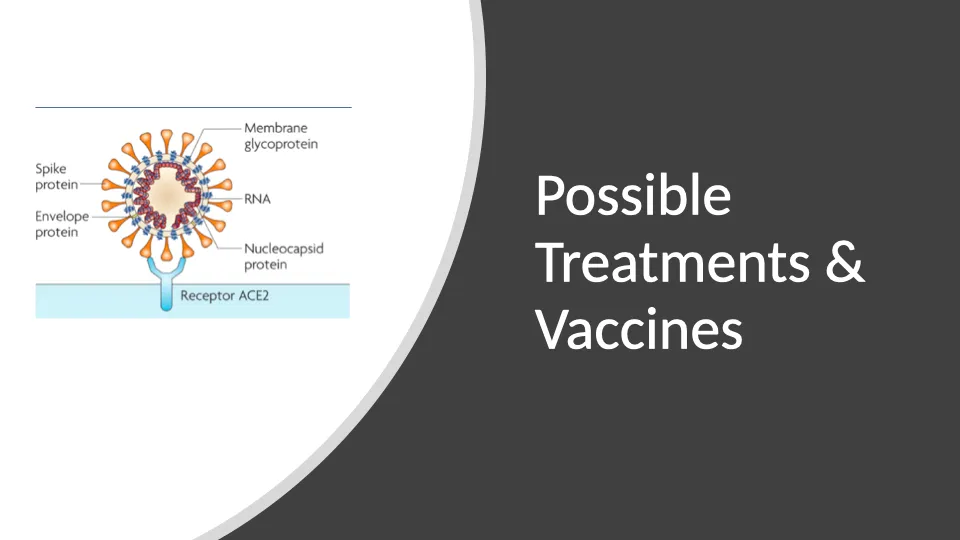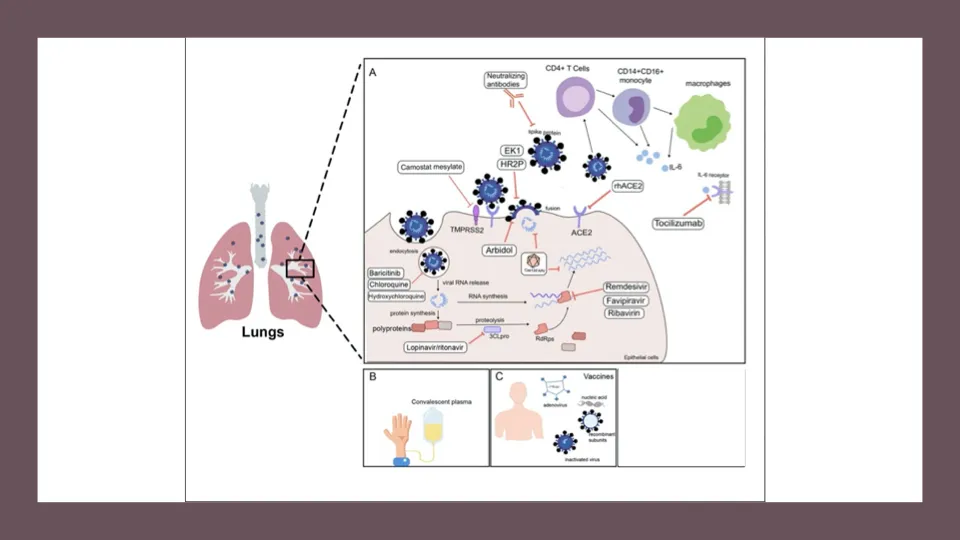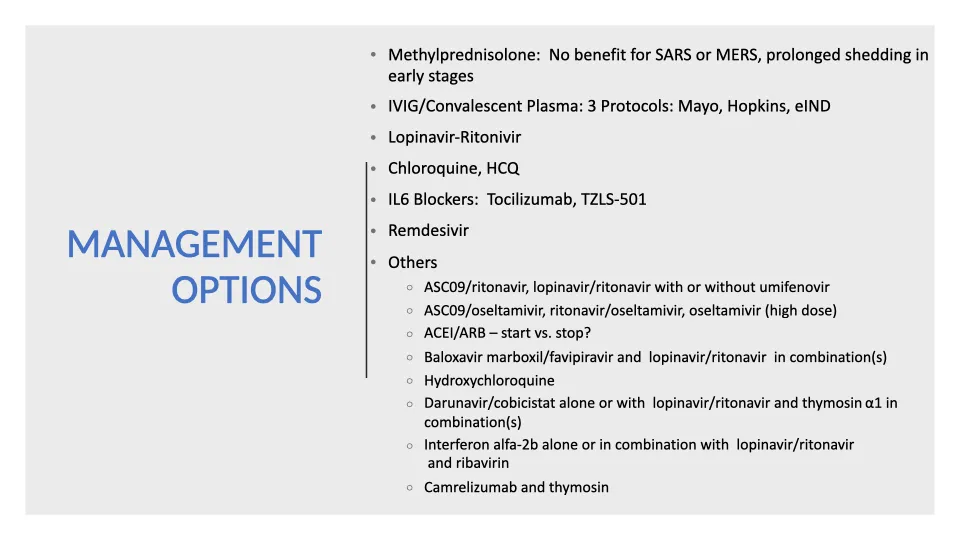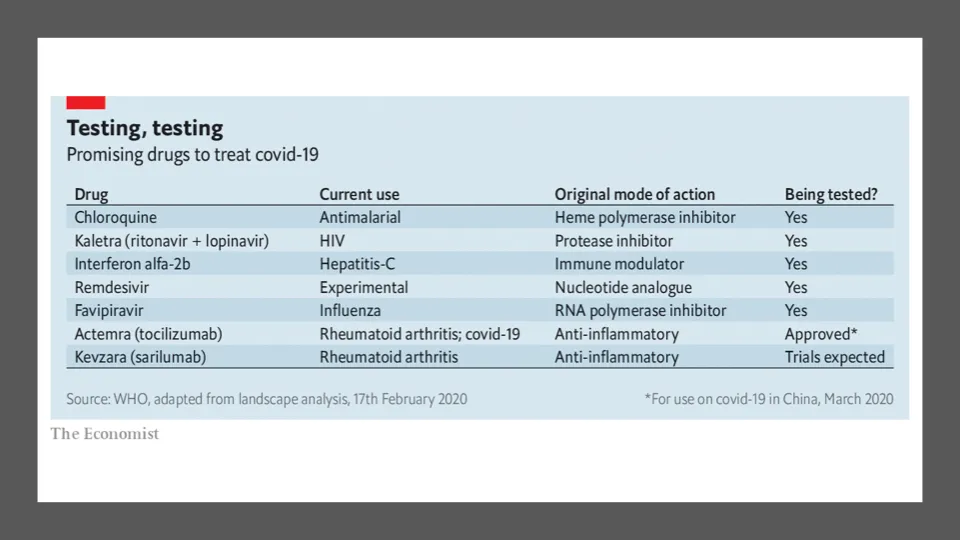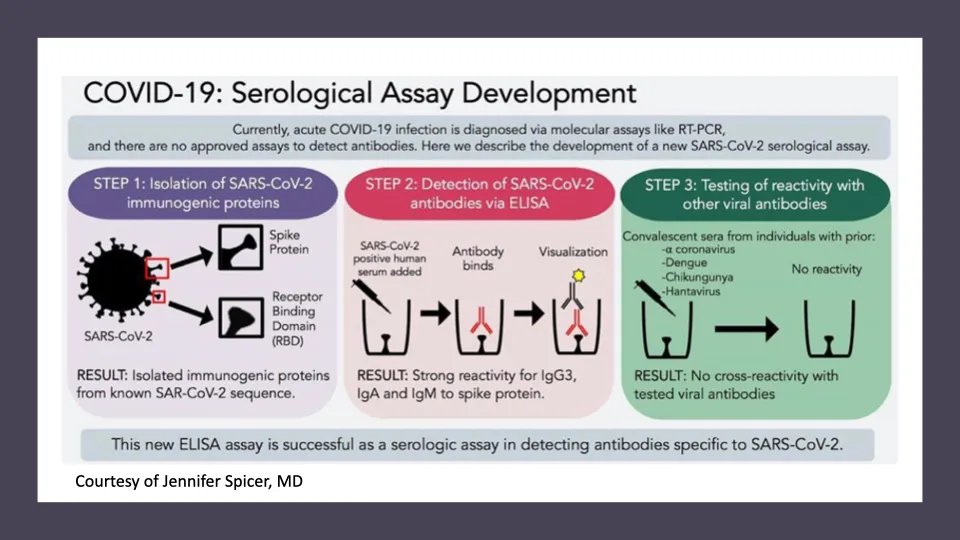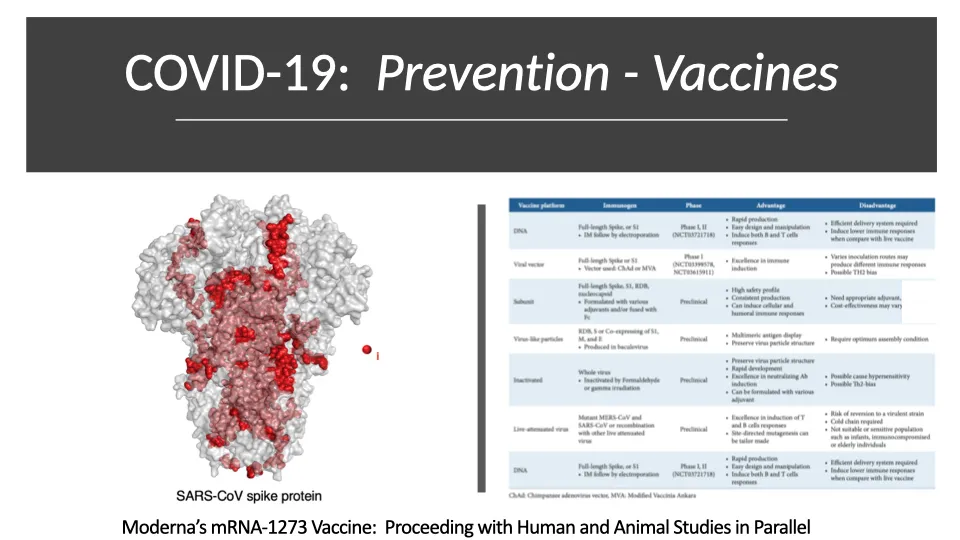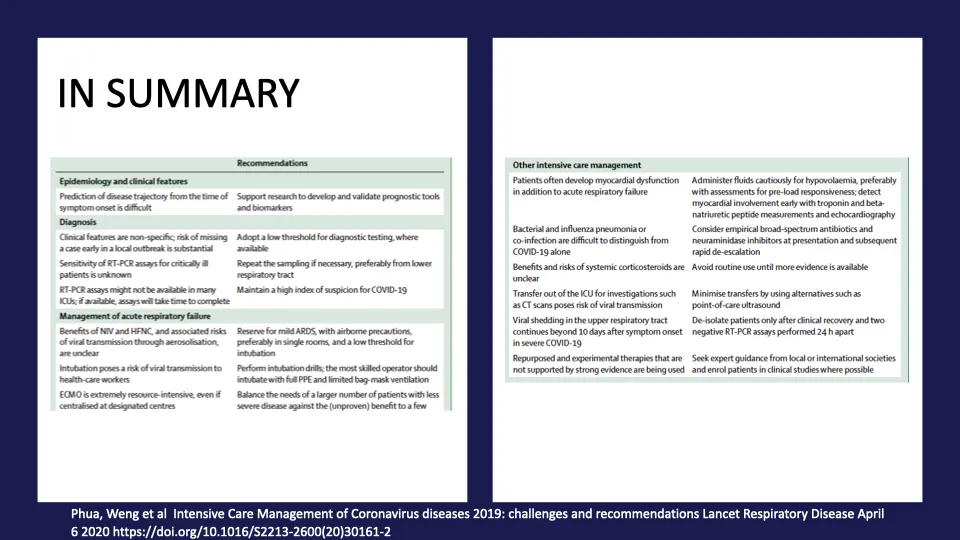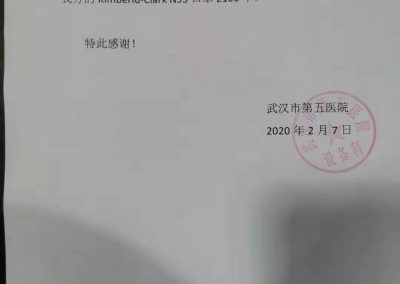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Information on the Coronavirus and how you can contribute.
关于COVID-19免疫接种的常见问题解答
自全球流行病爆发以来,联邦政府一直在开展曲速行动external icon计划,希望尽快提供一种或多种COVID-19疫苗。虽然CDC没有参与COVID-19疫苗开发工作,但一直与卫生部门和合作伙伴密切合作,为未来的疫苗制定免疫接种计划。CDC正在与包括医疗保健协会在内的各级合作伙伴合作,制定可适用不同疫苗和情形的灵活COVID-19免疫接种计划。
以下为常见问题回答。此部分将按需进行更新。
疫苗规划
曲速行动是卫生及公共服务(HHS)和国防部下属的合作计划,旨在帮助尽快研发、制作和分配数百万剂的COVID-19疫苗,同时确保这些疫苗安全有效。
曲速行动external icon的目标是交付有效的安全疫苗,首批供应将在2020年结束之前准备就绪。当前两种疫苗在美国获得了授权和建议,用于预防COVID-19。为帮助指导决策如何分配有限的首批COVID-19疫苗,CDC和免疫接种咨询委员会已经发布了应优先接种疫苗的群体 (见下) 建议。疫苗供应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我们的目标是随着大量疫苗的就绪,使每个人都能轻松获得COVID-19疫苗。然而在完成更多研究之前,COVID-19疫苗可能不适用于低龄儿童。
已有的分发计划
联邦政府对一个集中系统进行监督,以订购、分配和跟踪COVID-19疫苗。所有疫苗都将通过CDC订购。疫苗提供者将从CDC集中分销商处或直接从疫苗制造商处接收疫苗。
美国授权并推荐了两种疫苗,用于预防COVID-19,其他候选COVID-19疫苗正在开发当中。在大规模生产的同时也正在进行临床试验。随着现在首批疫苗的就绪,COVID-19免疫接种计划的规划和准备尤为重要。
规划工作着重于接种流程的每个步骤和细节,包括:
--作为CDC的COVID-19疫苗集中式输送系统的一部分,
与制造商和商业伙伴一起制定和检测物流计划
--协调从集中地点首次分发疫苗和所需物资
--首批疫苗出厂后,订购更多数量疫苗的流程
--在具体规定的温度下正确接收、储存和处理疫苗
--根据国家的建议决定,在疫苗数量不足以向每个人提供的时候,
应该由谁优先接种疫苗
--在全球流行病持续期间以安全的方式接种疫苗
--使用各种新的强化数据系统报告疫苗的库存、管理和安全性
--通过新的系统和其他信息源扩大安全性监测范围,
以及扩大现有安全监控系统
--制定评估疫苗有效性的计划, 也就是疫苗在现实生活中对预防COVID-19产生作用的程度
--围绕免疫接种计划各个方面的问题,
确保向公众和利益相关者传达及时、可信和清晰的信息
这种情况持续变化,随着新授权或批准疫苗的可用信息增加,规划也会相应推进。安全有效的COVID-19疫苗是美国应对策略的关键组成部分,以减少COVID-19相关疾病、住院治疗和死亡,并帮助社会职能恢复到COVID-19之前的状态。美国政府的目标是为选择在美国接种疫苗的所有人提供足够的COVID-19疫苗。
CDC的合作机构
州、领地和地方辖区: CDC与州、部落、领地和地方辖区合作为其相应辖区制定COVID-19免疫接种计划。CDC于2020年9月16日发布了战略手册,提供免疫接种计划制定期间需要考虑的具体信息。该战略手册pdf iconpdf icon于2020年10月30日更新。
私人合作伙伴和联邦机构:CDC还与私人合作伙伴(如独立药房的连锁店和网络)以及其他联邦机构(如印第安人卫生服务所)合作,计划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分发COVID-19疫苗。例如,CDC正在与药房合作,为长期护理环境中的住户提供现场COVID-19免疫接种服务,其中包括专业护理机构、疗养院以及大多数住户超过65岁的辅助生活设施。
疫苗是否足够所有人使用
目前,美国有两种疫苗获得授权和推荐,以预防COVID-19。为帮助指导决策如何分配有限的首批COVID-19疫苗供应,CDC和免疫接种咨询委员会发布了应优先接种疫苗的群体建议。 很多人对此存疑是情理之中的,特别是对于该病毒重病高风险人群及其亲人来说。
我们的目标是在COVID-19疫苗大量就绪时让所有人都可以轻松获得疫苗。这就是为什么在疫情应对早期,联邦政府开始筛选疫苗制造商external icon,帮助他们增加其快速制造和分配大量COVID-19疫苗能力的原因。这将让美国一开始就有尽可能多的疫苗可用,并在之后的数周和数月内持续增加供应。我们的目标是在COVID-19疫苗大量可用时让所有人都可以轻松获得疫苗。人们可使用数千家免疫接种提供者,包括医生办公室、零售药店、医院和具备联邦资质的卫生中心。
疫苗开发
**目前有多少种COVID-19疫苗正处于研制阶段?
当前,两种mRNA疫苗获得授权和推荐,用于预防COVID-19:
辉瑞-生物科技COVID-19疫苗
莫德纳COVID-19疫苗
多种COVID-19疫苗也仍然在开发当中。在美国,另外两种COVID-19疫苗的大规模(第3阶段)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或计划中。
**以前是否研制过冠状病毒疫苗?对其了解是什么?以及是否有助于如今的COVID-19疫苗研制?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是由冠状病毒引起的两种疾病,与COVID-19致病病毒密切相关。这两种疾病分别于2003年和2012年被发现,之后研究人员开始了疫苗的研发。没有任何SARS疫苗完成了第一阶段的研发和检测,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病毒消失后研究兴趣的降低所造成。一种MERS疫苗(MVA-MERS-S)在2019年成功完成了第1期临床试验。从早期疫苗研究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已被用于制定这次COVID-19疫苗的开发策略。
**为什么开发COVID-19疫苗耗时如此久?N1N1流感疫苗的开发只需要几个月而已。
当发现新的流感毒株(如2009年的H1N1流感疫苗)时,疫苗制造商可以使用与生产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相同的过程,从而节省宝贵的时间。与流感不同,冠状病毒还没有获得许可的疫苗或继续研发的流程。另外,COVID-19致病冠状病毒是一种新病毒,因此必须研发和测试全新的疫苗,以确保它们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疫苗测试和批准过程有许多步骤。美国多个机构和团体external iconexternal icon都在共同努力,以确保尽快获得安全有效的COVID-19疫苗。
疫苗接种
**在美国,两种获得授权和推荐用于预防COVID-19的疫苗均需要接种两针以产生药效。在美国,还有处于第3阶段临床试验的COVID-19疫苗,仅需一针。
**CDC建议疫情期间与同住者以外的人接触时、在医疗机构以及接种任何疫苗(包括COVID-19疫苗)时,都需要佩戴口罩遮掩口鼻。任何呼吸困难或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无法取下口罩的人不应佩戴口罩。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佩戴口罩的注意事项。
**用美国纳税人的钱购买的疫苗将免费提供给美国人民。但是,免疫接种提供者可以为某人注射疫苗并收取管理费。疫苗供应商可以向患者的公共或私人保险公司报销这笔费用,或者对于没有保险的患者而言,可以从卫生资源和服务管理局的供应商补助基金获得报销费用。
**CDC正在制定建议,当供应有限时,谁应优先获得COVID-19疫苗。为指导决策如何分配有限的首批COVID-19疫苗供应,CDC和免疫接种咨询委员会发布了建议,指导哪些群体应优先接种疫苗。我们的目标是在大量疫苗可用时让每个人都能轻松获得COVID-19免疫接种。
虽然CDC制定了谁应优先获得COVID-19疫苗的建议,但每个州都有其自己的疫苗优先、分配和配置计划。请联系您的州卫生部门获取关于其COVID-19疫苗计划的更多信息。
**无论是否已感染过COVID-19,都应为您提供COVID-19免疫接种。免疫接种前,您不应被要求接受抗体检测。
然而,当前感染COVID-19的人应等到疾病康复并达到解除隔离标准之后再接种疫苗。
此外,当前证据表明初次感染COVID-19病毒90天内的再感染并不常见。因此在需要的情况下,新近感染的人应将免疫接种推迟到90天之后。
**要阻止全球流行病疫情,人们需要使用所有可用的工具。疫苗与人们的免疫系统将共同发挥作用,以便在接触病毒之后,身体可以做好准备对抗病毒。佩戴口罩遮掩口鼻以及与他人保持至少6英尺距离等其他措施,也有助于减少接触病毒或将病毒传播给其他人的机率。COVID-19免疫接种和遵循CDC有关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建议结合使用,可以为防止感染COVID-19提供最佳保护。
**接种了两次疫苗以后还是需要戴口罩,并避免与他人密切接触, 虽然专家对COVID-19疫苗在现实生活中所能提供的保护有了更多了解,但对每个人来说,继续使用我们可用的所有工具来防止全球流行病仍然至关重要,例如佩戴口罩遮掩口鼻、勤洗手以及与他人保持至少6英尺的距离。将COVID-19免疫接种和遵循CDC有关如何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建议相结合,可以为防止感染和传播COVID-19提供最佳保护。专家需要更多地了解COVID-19疫苗所提供的保护,才能决定是否可以更改每个人为减缓导致COVID-19病毒的传播而应采取的措施的建议。其他因素,包括接种疫苗的人数以及病毒在社区内的传播方式,也会影响这一决定。
**流感疫苗不能保护您免于感染COVID-19,但可以防止您在感染COVID-19的同时感染流感,从而避免您的病情加重。虽然无法确切表明冬季的病毒传播趋势,但CDC认为流感病毒和导致COVID-19的病毒都有可能在这段时间内传播。这意味着接种流感疫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由于感染而获得的保护(称为自然免疫)程度因疾病而异且因人而异。由于此病毒为新发病毒,我们还不知道自然免疫会持续多长时间。当前证据表明COVID-19病毒在初次感染90天之内的再感染并不常见。
**至于免疫接种,在我们有可用疫苗并且掌握关于其功效的更多数据之前,我们无法得知免疫接种保护可以持续多长时间。
自然免疫和疫苗引发的免疫都是专家们正在努力研究的重要COVID-19课题内容,而CDC会在出现可用新证据时告知公众。
安全
**CDC和FDA鼓励公众向疫苗不良反应报告系统(VAERS)external iconexternal icon报告可能的副作用(称为不良反应)。此国家系统将收集这些数据,以查找意外出现、似乎比预期发生得更频繁、或具有异常发生模式的不良反应。了解疫苗副作用和不良反应之间的区别。向VAERS报告可帮助CDC监测疫苗的安全性。安全性是重中之重。
医疗服务提供者将被要求向VAERS报告接种疫苗后的某些不良反应。在任何紧急使用授权期间,医疗服务提供者还必须遵守根据FDA授权使用条件修订的任何安全报告要求;这些要求将公布在FDA的网站external iconexternal icon上。
CDC还在实施一种基于智能手机的工具v-safe,以便在人们接种COVID-19疫苗后跟进其健康状况。当您接种疫苗时,您应该还会收到一份 v-safe信息表,告诉您如何注册 v-safe。注册之后,您将定期收到以短信形式发来的调查问卷,以报告接种COVID-19疫苗后的任何问题或不良反应。
疫苗数量有限时,谁应优先接种疫苗
**医疗人员和长期护理设施住户应优先接种COVID-19疫苗(1a)
**下一阶段应接种疫苗的人群(1b和1c)
CDC建议,在可能重叠的1b阶段和1c阶段,应为以下人群提供免疫接种。CDC于2020年12月22日提出此建议。
1b阶段
· 一线基本工作人员,如消防员、警察、狱警、食品和农业员工、美国邮政服务员工、制造业员工、杂货店员工、公共交通服务员工,以及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教师、辅助人员和日托员工)。
· 75岁及以上人群,原因是他们因COVID-19住院、患病和死亡的风险很高。年龄在75岁及以上并且也是长期护理机构住户的人员应在1a阶段就接受免疫接种。
1c阶段
· 65-74岁人群,原因是他们因COVID-19住院、患病和死亡的风险较高。年龄在65-74岁同时也是长期护理机构住户的人员应在1a阶段就接受免疫接种。
· 年龄在16-64岁之间且患有基础疾病的人群,原因是他们因COVID-19而患上严重威胁生命的并发症的风险较高。
· 其他基本工作人员,如交通物流、食品服务、住房建设和金融、信息技术、通信、能源、法律、媒体、公共安全、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工作人员。
**随着疫苗可获得性增加,将会扩大免疫接种建议范围以覆盖更多人群
目标是当足够数量的疫苗准备就绪,每个人都能方便地接种COVID-19疫苗。疫苗供应增加但数量仍然有限,ACIP将逐步扩大推荐免疫接种的群体
from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faq.html
美国又一新冠疫苗效果达94.5%
- 初步分析发现志愿者中有95例确诊COVID-19(5例病人在用疫苗组;90例病人在安慰剂组);15例是65岁以上,20例是多种族(12例拉丁裔,4例非裔美国人,3例是亚裔美国人,1例是多种族混血。);
- 疫苗功效为94.5% (Pfizer公司的类似疫苗>90%);
- 3期临床试验研究统计学意义显著(p <0.0001)
- 比Pfizer的mRNA疫苗更容易保存;在2-8度可保存30天;-20度可保存6个月;Pfizer需要用干冰保存,较难运送。
- 也是要打两次注射;
- 对预防重症有效,发现的11例重症病人全部在安慰剂组;
- 没有发现有任何严重的安全问题。主要的一些常见不良反应均属轻微的中度,基本上都能耐受,且持续时间很短。首剂给药后,大于或等于2%的3级(严重)事件包括:注射部位疼痛(2.7%);第二次给药后包括:疲劳(9.7%),肌痛(8.9%),关节痛(5.2%) ),头痛(4.5%),疼痛(4.1%)和注射部位的红斑/发红(2.0%)。
- Moderna打算在未来几周内向美国FDA申请紧急使用授权(EUA),并希望该EUA是基于对151例病例的最终分析(平均随访时间超过2个月)。
群体免疫与SARS-Cov-2 的意义
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也称为间接保护,社区免疫或社区保护(indirect protection, community immunity, or community protection),是指当种群中有足够比例的免疫个体时,那么易感个体会免受感染而受到保护。换句话说,群体免疫是由于缺乏大量的易感个体,因此受感染的个体无法使流行病继续传播。它源于通过自然感染或接种疫苗获得的个体免疫力。群体免疫一词最初是在一个多世纪前引入的。在20世纪后半叶,随着计划免疫的扩大,对免疫覆盖率目标的制定,消除疾病的讨论以及对疫苗接种计划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的需要,该术语的使用变得更加普及。
天花的消灭,成人及儿童常规乙型流感嗜血杆菌结合疫苗和肺炎球菌疫苗接种后疾病的持续减少, 都是疫苗诱导的群体免疫成功的例子。
群体免疫阈值(Herd Immunity Threshold)
群体免疫阈值定义为已获得免疫力而不再参与传播链的人口比例。如果人群中免疫个体的比例超过此阈值,则当前的流行病爆发将会被扑灭,病原体的流行传播将被中断。在最简单的模型中,群体免疫阈值取决于基本繁殖数(R0;在完全易感人群中一个被感染者去感染别人的平均人数),群体免疫阈值计算为1- 1 / R0(图)。有效繁殖数量包括部分免疫种群,并解释了种群中易感个体比例的动态变化,例如在暴发期间或大规模免疫后所见。高度易传染的病原体,例如麻疹,将具有较高的R0(12-18),并且必须有很大比例的人口免疫才能减少持续传播。自从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冠状病毒-2(SARS-CoV-2)大流行开始以来,大多数研究估计SARS-CoV-2 R0的范围为2到3.2。假设没有人群免疫力,并且所有个体都在没有任何干预措施的情况下,SARS-CoV-2的群体牛群免疫阈值在同等易感性和同等感染性范围内可望达到50%至67%。
图:不同疾病的群体免疫阈值
图中位置是测量阈值时的位置。
保护期限
对于自然获得的免疫和疫苗诱导的免疫,免疫记忆的持久性是决定种群保护水平和维持种群免疫的关键因素。对于麻疹,水痘和风疹,无论是感染还是疫苗接种都可以实现长期免疫。对于季节性冠状病毒,尚未观察到是否为持久免疫或是短期免疫。对于产生短暂免疫的感染,易感人群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会很快增加,并再次爆发。通过有效的疫苗和疫苗计划,只要社区保持必要的水平,就可以保持群体免疫(即使需要定期进行疫苗接种),也可以减少疫情暴发。
异质性的作用
群体免疫阈值是假定人口中个体之间的随机地混合。但是,日常生活更加复杂。个体并非是随机地混合在一起,并且某些个体的互动次数会比其他人多。经过经验验证的网络模型表明,具有较高频率交互作用的个体在疫情暴发时更早受到感染。这可能会导致感染在达到所谓的群体免疫阈值之前减慢社区传播速度。然而,关于社会混合中异质性对群体抗SARS-CoV-2免疫的确切影响尚不确定。
T细胞交叉反应
T细胞是免疫力的重要介体。最近的报告表明,与其他冠状病毒的交叉反应性可能会赋予人群相对的保护,使其免受冠状病毒病-2019的侵害(COVID-19)。T细胞交叉反应性是否可以提供杀毒性免疫力(即宿主不能携带或传播感染),还是只降低疾病的严重程度尚不清楚。
基于感染的群体免疫政策
有些人已经提出了一种基于感染的群体免疫方法(即,在“隔离”易感人群的同时,让低风险人群被感染),以减缓SARS-CoV-2的传播。但是,这样的策略会有风险。例如,即使感染死亡率不高,一种新的病原体也会导致相当大的死亡率,因为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人口对病原体没有免疫力。隔离高风险人群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最初在低死亡率人群中传播的感染最终可能会传播到高死亡率人群中。此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大规模成功的基于故意感染的群体免疫策略的例子。
只有极少数情况通过感染获得了看似持久的群体免疫力。最新的和有据可查的例子与巴西萨尔瓦多的Zika有关。在COVID-19大流行初期,随着欧洲其他国家在2020年2月下旬和2020年3月初关闭了人们活动,瑞典做出了禁止关闭的决定。最初,一些地方当局和记者将其描述为群体免疫策略:瑞典将尽最大努力保护最弱势群体,但其目的是让足够数量的公民受到感染,以实现基于感染的真正群体免疫。到2020年3月下旬,瑞典放弃了这一战略,转而采取积极干预措施。大多数大学和高中都对学生关闭,实行了出行限制,鼓励在家工作,并颁布了禁止50人以上的团体的规定。据报道,到2020年4月,瑞典斯德哥尔摩的血清阳性率远未达到群体免疫的水平,不到8%,与其他几个城市(即瑞士的日内瓦和西班牙的巴塞罗那)相当。
美国的人口约为3.3亿。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感染致死率0.5%的估计,美国大约需要1.98亿人才能免疫以达到大约60%的群体免疫阈值,这将导致数十万人的额外死亡。假设到目前为止,只有不到10%的人口被感染,其感染诱导的免疫力持续2到3年(持续时间未知),此时控制感染大流行是不现实的。SARS-CoV-2疫苗将有助于达到群体免疫的阈值,但是疫苗的有效性和疫苗覆盖率尚待观察。
结论
群体免疫是抵抗流行病暴发的重要防御手段,并在疫苗接种率令人满意的地区取得了成功。重要的是,即使是很小的保护水平偏差,也可能由于易感人群的局部集群而导致重大疫情爆发,就像过去几年中的麻疹一样。因此,疫苗不仅必须有效,而且疫苗接种计划必须有效并且广泛采用,以确保仍然不能直接受到保护的人仍能获得相对保护。
Covid-19与肾脏疾病COVID-19大流行遇到流感季
到限制,因为这种方法需要每患者每天使用2个透析过滤器(标准CKRT为每2.5至3天使用1个透析过滤器)。由于预混,袋装CKRT流体的供应有限,一些中心开始探索使用其标准间歇性透析机,透析液浓缩物和透析水系统生成透析液。此外,由于COVID-19患者的高凝性,抗凝方案也得到迅速发展。
远程医疗被提供肾脏疾病患者护理的临床医生和中心迅速采用。尽管远程医疗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资源,但对其长期使用仍存在一些担忧。例如,《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指南》和付款规定激励医生每月在透析过程中亲自进行4次血液透析的病人。尽管这种频繁访问的价值仍然不确定,但是远程医疗是否适合此弱势人群尚不清楚。如果没有临床医生,临床检查(至关重要的是确定体积状态),与透析相关的实验室研究的审查,流程图(非现场从业人员可能无法获得)以及与护理人员的交流显然可能不太全面。实际存在。
Covid-19 与各科系列链接:
Corresponding Author: Wolfgang C. Winkelmayer, MD, MPH, ScD, Section of Nephrology,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One Baylor Plaza, Ste ABBR R705, MS 395, Houston, TX 77030 (winkelma@bcm.edu).
Conflict of Interest Disclosures: Dr Winkelmayer reported receipt of personal fees from Akebia, AstraZeneca, Bayer, Daichii-Sankyo, Janssen, Merck, Relypsa, and Vifor Fresenius Medical Care Renal Pharma and grants from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Dr Charytan reported receipt of personal fees from PLC Medical, Janssen, GlaxoSmithKline, Merck, and Fresenius; grants and personal fees from Gilead, AstraZeneca, and Amgen; and grants from Bioporto. No other disclosures were reported.
Viewpoint
Nephrology and COVID-19
COVID-19大流行遇到流感季
COVID-19大流行遇到流感季
风城黑鹰编译
在Covid-19 大流行期间,秋天又快到了, 秋冬天意味着流感季节的到来。每年的流感流行严重影响着全球的卫生保健系统,自2010年以来,仅在美国每年就导致12 000至61 000例死亡。在任何给定年份,流感发病率和死亡率的程度反映了流感病毒的主要毒株中基因漂移或转移的程度, 流感疫苗的功效和覆盖范围。随着冠状病毒病-19(COVID-19)大流行,临床医生面临第二种呼吸道病毒,其发病率和死亡率比流感高几倍,部分原因是Covid-19在未受过免疫的人群中传播。认识流感和COVID-19同时流行迫在眉睫,对人类的威胁是公共卫生官员和临床医生的主要关切的问题。
人群方面考虑:
虽然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冠状病毒-2(SARS-CoV-2)(引起COVID-19的病毒)和流感是截然不同的病原体,但两者也有重要的重叠区域(表)。
这两种病毒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因此,预计采用非药物干预(NPI),例如在公共场所使用强制性的面部遮盖物,关闭学校和零售场所以及限制行动,都将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两种病毒感染的发生率。研究一致表明,采用NPI措施后,2020年(1月至5月)的流感发病率与往年相比下降得比预期的要早。解释这些数据时应谨慎,因为在最初的大流行期间,非SARS-CoV-2呼吸道病毒的检测数量也大大降低了。
假如人们一直坚持遵守使用NPI,那么预期流感传播途径减少的这个趋势将会持续到下一个流感季节。在传播增加期间继续使用面罩和恢复局部封锁可以大大降低两种疾病的感染率,但是随着行动限制的放宽,预计流感和SARS-CoV-2的传播都将增加。
除了非传染性疾病外,季节性流感疫苗的接种对降低人群中病毒库的重要性也越来越重要。尽管可以广泛使用多种流感疫苗,但成人的国家疫苗接种率始终低于50%。国家教育运动与基于社区的疫苗接种计划相结合,这些计划的重点是获得保健服务的人群较少,以及年轻人吸收率较低的人群(如年轻人),对于将覆盖率提高到过去几年的水平至关重要。
对临床实践的影响
尽管没有特定的临床表现能可靠地区分早期流感和COVID-19,但在临床实践中确诊是什么病毒很重要。
首先,两种病毒的管理方法不同。可以用神经氨酸酶抑制剂或帽依赖性核酸内切酶抑制剂治疗流感,但它们都不具有抗SARS-CoV-2的抗病毒活性。瑞姆昔韦可在紧急使用授权下用于治疗COVID-19,但由于它是肠胃外给药的,因此仅可供住院患者使用。确认COVID-19的诊断也很重要,特别是对于那些可能对瑞姆昔韦有禁忌症的患者,确诊可鼓励这些病人早期参与临床试验,参与研究COVID-19的许多其他治疗方法,包括可能对门诊治疗产生重要影响的口服抗病毒药。
其次,由每种病毒引起的综合症遵循不同的发病过程。流感患者通常在疾病的第一周经历最严重的症状,而COVID-19的患者可能会经历较长的症状持续时间,并在疾病的第二或第三周达到高峰。区分流感与新冠病毒可以使临床医生为患者提供有关预期症状如何演变的指导,并可以帮助确定疾病后期的并发症。
第三,正确识别病毒具有重要的感染控制意义,包括有关隔离和检疫的适当指导,返校和工作建议,以及COVID-19病例识别和接触者追踪。
随着2020年呼吸道病毒季节的开始,任何表现出呼吸道病毒感染非特异性特征的患者都应至少接受SARS-CoV-2的检测,这与以往通常仅根据临床标准进行治疗的实践有所不同。复杂性的另一个方面是,已观察到与流感和SARS-CoV-2共同感染病例,因此一种病毒的阳性结果并不排除同时有另一种病毒的感染。目前尚不清楚初始检测是否应同时包含两种病毒或是否同时包含两种病毒SARS-CoV-2结果返回后可以添加流感检测。首选的诊断算法将取决于在本地可以使用哪些诊断测试,并仔细考虑测试特性,成本,周转时间和供应链问题。
由于小儿病毒的几个独特特征,因此管理儿童群体的方法可能有所不同。流感是儿童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的来源,人们认为5至17岁的个体在季节性流感流行中起着关键作用,儿童中COVID-19的疾病轨迹通常是与流感相反,因此尽管监测儿科传播的COVID-19对于指导学校和托儿所重开计划仍然很重要,COVID-19对儿童的健康影响有望远低于老年人。
不断发展的诊断环境
对SARS-CoV-2的大规模监控已成为控制COVID-19大流行的基石。可以通过验证替代标本类型(例如前鼻拭子和唾液)来扩大诊断测试的范围,这些标本类型可以提高收集和分发快速即时诊断信息的便利性。这两种方法都将有助于进行串行测试,从而可以改善病例检测,从而减少无症状和症状前的蔓延,个人防护设备的使用以及隔离的时间。重要的是,许多制造商正在修改现有的检测方法,以允许使用单个试剂盒对流感,SARS-CoV-2和呼吸道合胞病毒进行多重检测。这些测试可以帮助满足临床医生对有效诊断感染的重要需求,同时最大程度地降低风险和对患者和员工的不便。当然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工作来验证这些测定是否可与唾液一起使用以及在护理时使用。
结论
尽管在SARS-CoV-2诊断,治疗和疫苗开发领域取得了快速进展,但该人群仍然容易受到并发流感和COVID-19流行病的影响。发病率和死亡率的规模将直接关系到公共卫生应对的力度,这必须强调目前可用的两种最有效的预防感染工具的重要性:广泛实施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和保持非药物干预(NPI)直至获得社区免疫,后者要通过有效的SARS-CoV-2疫苗和/或自然感染实现。作为临床医生和社区的成员,医生和其他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应促进这些重要的干预措施,并在前所未有的挑战时期保持灵活的诊断方法。
我的电报频道:https://t.me/joinchat/AAAAAFM7zGSUbl4cRMBM3A
Article Information
August 14, 2020
Influenza in the COVID-19 Era
Daniel A. Solomon, MD1; Amy C. Sherman, MD1; Sanjat Kanjilal, MD, MPH1,2
Author Affiliations Article Information
JAMA. Published online August 14, 2020. doi:10.1001/jama.2020.14661
Corresponding Author: Daniel A. Solomon, MD, Divis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75 Francis St, Boston, MA 02115 (dasolomon@bwh.harvard.edu).
Published Online: August 14, 2020. doi:10.1001/jama.2020.14661
Conflict of Interest Disclosures: None reported.
纽约医护人员新冠感染率近14%
几个月前,纽约还是新冠流行的风暴眼,现在得让位于加州,佛州及德州了。
那么回头总结一下,纽约那些日子里,拚命抗疫的医院里医护人员有多少已感染了新冠呢?
北威尔(Northwell)医疗系统是是纽约州的最大的医疗系统。他们为此做了一个调查。
从2020年4月20日到2020年6月23日期间,北威尔的医疗系统给他们的职员提供了免费的自愿性的抗体检测。这包括北威尔系统的在大纽约市的52个医疗定点地方。主要的目的是看看有多少有抗体阳性存在。这些抗体阳性预示着他们已经曾经有过新冠的感染。
北威尔医疗系统一共邀请了70812个雇员参与,截至2020年6月23日,共有46117 65%的人获得了检测。最后有效的检测人数是40329人。参与的人数中包括70%的女性,6%的黑人, 0.8%的多种族, 14%是拉丁裔。28%是护士,9.3%是医生。其中亚裔有6082人。
这个研究结果发现,北威尔医疗系统的医务人群中抗体阳性占13.7%,而且这个数字和普通的纽约地区的随机抽样的人群感染率是非常相似的( 14% )。当然,这两个感染率都高于洛杉矶地区的感染率(4.1%)而且他们血清阳性抗体的阳性率和以前核酸检测的阳性率是高度相关的(即当时核酸检测阳性者,现在抗体检测也基本是阳性)。
研究发表在JAMA:
August 6, 2020
Prevalence of SARS-CoV-2 Antibodies in Health Care Personnel in the New York City Area
Joseph Moscola, PA, MBA1; Grace Sembajwe, DSc, MSc, CIH2; Mark Jarrett, MD, MBA, MS1; et al
Author Affiliations
JAMA. Published online August 6, 2020. doi:10.1001/jama.2020.14765
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重新开放K-12学校 ——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研究院的报告
Kenne A. Dibne
风城黑鹰编译
冠状病毒病-19(COVID-19)大流行给全(美)国幼儿园-12年级教育系统(K-12)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为应对大流行,导致全国各地的教学楼急匆匆地关闭,几乎没有时间确保教学的连续性或创建一个框架来决定何时以及如何重新开设学校。各州和学区现在正在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即在Covid-10社区传播方式迅速变化的背景下,是否应该以及如何重新开放学校。 为响应以证据为基础(循证)的指南以支持教育决策者的需求,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研究院召集了一个专家委员会,为2020-2021年学校的中小学重新开放和安全运营提供学年指导。考虑到当地学校和社区的政治和实际情况,委员会要求将医学和公共卫生方面的最新证据与有关最适合儿童和青年的证据相结合。委员会的报告《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重新开放K-12学校:优先考虑健康,公平和社区》提供了一系列建议,旨在帮助各州和学区确定是否开放学校进行入校面对面地学习,如何降低传染的危险。还要确定那些迫切需要进行研究的领域,以使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能够针对大流行期间的重新开放和运营学校做出循证决策。 委员会认识到重新开放学校建筑物的决定需要权衡开放后的公共卫生风险与不开放(保持学校关闭)所带来的教育风险及其他风险。随着学区对这些风险的考虑,委员会建议学区尽一切努力优先考虑重新开放,重点是向幼儿园至5年级的学生以及有特殊需要的学生提供面对面的授课。 该委员会强调应为年幼的孩子提供面对面的指导是出于这几个原因:首先,委员会做出了这样的假设:即使校舍关闭,教学仍将通过远程学习继续进行。小学学龄儿童以及有特殊医疗保健需求的儿童在远程学习上可能会遇到困难,尤其是在成人无法随时监督学习的情况下。幼儿园至三年级的孩子们仍处在发展调节自己的行为和情绪,保持注意力并监督自己的学习所需的技能中。此外,研究表明,对于到三年级时还未能阅读的孩子来说(特别是对于低收入家庭)有着长期的,不良的后果。这表明确保低年级儿童的高质量教育体验是至关重要的。 重新开放学校对家庭和社区也有潜在的好处,包括获得就餐计划,一些医疗保健服务和精神心理保健服务。尽管孩子照顾不是学校的主要职能,但在2020年春季关闭学校期间,家庭和社区的经历清楚地表明,在家长外出工作时,学校在为儿童提供安全和成长的空间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尽管为学生,家庭和社区重新开放学校的好处显而易见,但教育领导者还必须考虑学校人员和学生家庭的健康风险,以及安全运营所需的缓解策略的实用性和成本。校舍状况因学校而异, 如何确保学校学生和教职工健康是另一个复杂的问题。为了安全地重新开放,鼓励学区确保通风和空气过滤,经常清洁表面,提供定期洗手的设施,并为社交距离提供空间。实施这些全套战略将耗资巨大,并且需要解决许多实际挑战。在校舍老化和预算有限的学区,实施所有推荐策略特别困难。联邦或州政府应为这些缓解策略提供资金来源。 考虑到学区需要做出的决策很复杂,委员会提出了一些建议,旨在确保在决策过程中平衡公共卫生和教育专业知识,决策过程考虑了学区社区的价值和需求。 该委员会呼吁学区和公共卫生官员之间建立伙伴关系,以便可以根据现有的最佳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数据和证据来重新制定决策,在学校建筑物开放时减轻病毒传播的计划以及有关未来关闭的决定。这应包括监测和评估流行病学数据,以迭代方式评估社区里的疾病活动。特别令人关注的指标包括确诊的COVID-19的新病例数,新的住院和死亡人数,以及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冠状病毒2(SARS-CoV-2)阳性诊断检验的百分比。 学区还需要监测缺勤情况,并警告公共卫生官员人数的缺勤人数大幅增加。委员会认识到,例如在农村地区的某些社区,公共卫生办公室人手不足或缺乏在传染病方面具有广泛专业知识的人员。考虑到这一点,委员会建议各州发挥领导作用,以确保学区能够获得做出这些关键决定所需的公共卫生专业知识。 随着全国范围内对重新开放问题的强烈关注表明,学校关闭的影响超出了对学生,教师和家庭所带来的后果。考虑到这一点,委员会建议学区建立一种机制,例如当地工作队,以允许学校职员,家庭,当地卫生官员和其他社区利益的代表提供意见,以告知有关重新开放学校的决定。该跨部门工作组应建立一个地方决策框架,以引起广泛关注:(1)建立社区的价值观,目标和重开放学校的优先事项;(2)审查缓解策略和政策选择(3)建立协议以收集和监视社区中与COVID-19环境有关的数据,以便可以做出必要的决定来改变路线或在必要时关闭校舍。在此过程中,相关决策者需要为这些数据的含义建立明确的阈值;例如,某学校看到达到某个特定数量的情况下,就会制定相应的政策以应对。 这些工作组还需要考虑以下事实的透明沟通:可以采取措施降低学校重新开放时传播COVID-19的风险,但无法完全消除这种风险。分担不同情况的风险和利益,并考虑可以实施的干预措施,并与家人沟通,为确保子女在学校的安全做出一切努力,这一点至关重要。尽管各方不一定都同意有关何时以及如何重新开放学校的最终决定,但包容性过程可能有助于建立对学校领导的信任,以便在条件变化时可以迅速执行决定。 与COVID-19相关的证据基础上的空白(数据不足)使教育领导者以及州和地方政策制定者面临的这些无数决定变得更加困难。该委员会确定了许多重要的研究问题。目前,关于儿童在将COVID-19彼此传播或传播给成人方面的作用,目前尚无科学共识。关于这一点的更好证据将为决策者提供急需的指导。同样,还需要研究重新开放学校在促进SARS-CoV-2社区传播中的作用,SARS-CoV-2气溶胶传播的潜在风险以及缓解SARS-CoV-2传播策略的相对有效性。这些研究问题应与重新开放学校的过程一起解决。 该报告认识到承认重新开放学校的决定是在长期教育不平等以及与COVID-19相关的结果造成严重困扰的情况下做出的,这一点很重要。正如公立学校满足其社区需求的能力取决于可用资源一样,社区应对COVID-19危机的能力也取决于医疗基础设施和医疗服务的获取。这些挑战有可能以对最脆弱的社区来说是灾难性的方式相互加剧。在重新开放问题的任何答案中,决策者都需要通过确保传统上边缘化的声音参与决策过程,获得必要的服务以及公平地分配资源,将公平放在决策应对的中心。此刻是重新开放学校的机会,使学校能够更好地为依赖学校的学生,家庭和社区服务。 Article Information Reopening K-12 School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pandemic has presented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to the nation’s kindergarten-grade 12 education system.1 The rush to respond to the pandemic led to closures of school buildings across the country, with little time to ensure continuity of instruction or to create a framework for deciding when and how to reopen schools. States and school districts are now grappling with the complex questions of whether and how to reopen school buildings in the context of rapidly changing patterns of community spread. In response to the need for evidence-based guidance to support education decision makers, the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convened an expert committee to provide guidance on the reopening and safe operation of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for the 2020-2021 school year. The committee was asked to integrate the most up-to-date evidence from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 with evidence about what is best for children and youth in view of the political and practical realities in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The committee’s report, Reopening K-12 School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Prioritizing Health, Equity, and Communities, provides a series of recommendations aimed at helping states and school districts determine both whether to open school buildings for in-person learning and, if so, how to reduce risk in the process of reopening.2 It also identifies areas of research that are urgently needed to allow educators and policy makers to make evidence-based decisions about reopening and about operating schools during a pandemic. The committee recognized the decision to reopen school buildings entails weighing the public health risks of opening against the educational and other risks of keeping buildings closed. As school districts weigh these risks, the committee recommended that the school districts make every effort to prioritize reopening with an emphasis on providing in-person instruction for students in kindergarten-grade 5 as well as those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who might be best served by in-person instruction. The committee emphasized providing in-person instruction for children in the younger grades for several reasons. First, the committee made the assumption that even if school buildings remain closed, instruction will continue through distance learning. Elementary school–aged children as well as those with special health care needs, in particular, may struggle with distance learning, especially if an adult is not readily available to supervise the experience. Children in kindergarten-grade 3 are still developing the skills needed to regulate their own behavior and emotions, maintain attention, and monitor their own learning.3 In addition, research has demonstrated long-term, adverse consequences for children who are not reading at grade level by the third grade, particularly for those in low-income families. This suggests it is critically important to ensure quality educational experiences for children in the lower grades.4 There are also potential benefits to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of reopening school buildings, including access to meal programs, some health care services,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lthough childcare is not the primary function of schools, the experiences of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during school closures during the spring of 2020 make clear that schools serve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viding a safe and nurturing space for children while their caregivers work. Even though the benefits of reopening schools for students,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are clear, education leaders must also consider the health risks to school personnel and students’ families, as well as the practicality and cost of the mitigation strategies necessary to operate safely. Variation across schools in the condition of buildings is an additional complication for ensuring the health of students and staff at schools. To reopen safely, school districts are encouraged to ensure ventilation and air filtration, clean surfaces frequently, provide facilities for regular handwashing, and provide space for physical distancing. Implementing this full suite of strategies will be costly and will require addressing many practical challenges. In school districts with aging school buildings and limited budgets, it will be especially difficult to implement all of the recommended strategies. Funding for these mitigation strategies should come from federal or state sources. Recognizing the complexity of the decisions that school districts need to make, the committee outlined several recommendations aimed at ensuring a balance of public health and educational expertise is brought to bear in decisions, and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considers the values and needs of the community the school district serves. The committee called for partnerships between school districts and public health officials so that reopening decisions, plans for mitigating spread of the virus when buildings open, and decisions about future closures are all informed by the best available epidemiological and public health data and evidence. This should include a plan to monitor and evaluate epidemiological data to iteratively assess disease activity in the community. Indicators of particular interest include the number of new cases of COVID-19 diagnosed, the number of new hospitalizations and deaths, and the percentage of positive diagnostic tests for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 School districts also will need to monitor absenteeism and alert public health officials to any large increases.5 The committee recognized that in some communities, in rural areas, for example, public health offices are short-staffed or lack personnel with extensive expertise in infectious disease. With this in mind, the committee recommended that states take a leadership role in ensuring school districts have access to the public health expertise necessary to make these critical decisions. As the intense national focus on the reopening question reveals, school closures have implications beyond the consequences for students, teachers, and families. With this in mind, the committee recommended that school districts develop a mechanism, such as a local task force, that allows for input from representatives of school staff, families, local health officials, and other community interests to inform decisions related to reopening schools. This cross-sector task force should build out a local framework for decision-making that brings multiple voices to the table to: (1) establish the community’s values, goals, and priorities for reopening schools, (2) review mitigation strategies and policy options for schools, and (3) establish protocols for collecting and monitoring data related to the COVID-19 context in the community such that necessary decisions can be made to change course or reclose buildings if necessary. During this process, relevant decision makers need to establish clear thresholds for what those data mean; for example, once a school sees a specific number of cases, it will enact specific policies in response. These task forces also need to consider transparent communication of the reality that while measures can be implemented to lower the risk of transmitting COVID-19 when schools reopen, there is no way to eliminate that risk entirely. It is critical to share both the risks and benefits of different scenarios, and to consider interventions that can be implemented and communicate to families that every effort is being made to keep their children safe in schools. Although all parties will not necessarily agree with the final decisions about when and how to reopen schools, an inclusive process will likely help build trust in school leadership so that decisions can be implemented quickly should conditions change. These myriad decisions facing education leaders and state and local policy makers are made more difficult by gaps in the evidence base related to COVID-19. The committee identified a number of important research questions. Currently there is no scientific consensus on the role of children in transmitting COVID-19 either to one another or to adults. Better evidence on this point would offer much-needed guidance for decision makers. Similarly, research is needed on the role of reopening schools in contributing to community spread of SARS-CoV-2, the potential risk of airborne transmission of SARS-CoV-2, and the relative effectiveness of strategies for mitigating the spread of SARS-CoV-2. These research questions should be addressed concomitantly with the process of reopening schools. The report recognized the importance of acknowledging that decisions to reopen schools are occurring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 long history of inequity in education, as well as deeply troubling inequities in COVID-19–related outcomes. Just as the ability of public school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ir communities is contingent on available resources, so too is a community’s ability to respond to the COVID-19 crisis contingent on health care infrastructure and access. These challenges have the potential to compound each other in ways that could be catastrophic for the most vulnerable communities. Within any answer to the question of reopening, decision makers will need to position equity at the center of their response by ensuring traditionally marginalized voices are engaged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necessary services are accessible, and resources are equitably distributed. This moment is an opportunity to reopen schools in ways that enable them to better serve the students,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that rely on them. Corresponding Author: Kenne A. Dibner, PhD,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500 Fifth St NW, Washington, DC 20001 (kdibner@nas.edu).
A Report From the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Kenne A. Dibner, PhD; Heidi A. Schweingruber, PhD; Dimitri A. Christakis, MD, MPH
Published Online: July 29, 2020. doi:10.1001/jama.2020.14745
Conflict of Interest Disclosures: None reported.
Funding/Support: The study was funded by the Brady Education Foundation and the Spencer Foundation.
Role of the Funders/Sponsors: The Brady Education Foundation and the Spencer Foundation had no role in the preparation, review, or approval of the manuscript or decision to submit the manuscript for publication.
Additional Information: The report Reopening K-12 School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Prioritizing Health, Equity, and Communities was produced by the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The authors of this Viewpoint were the study director (Dr Dibner), director of the Board on Science Education (Dr Schweingruber), and a member of the study committee (Dr Christakis).
References
1. Sharfstein JM, Morphew CC. The urgency and challenge of opening K-12 schools in the fall of 2020. JAMA. 2020;324(2):133-134. doi:10.1001/jama.2020.10175
ArticlePubMedGoogle ScholarCrossref
2.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Reopening K-12 School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Prioritizing Health, Equity, and Communities.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20.
3.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Shaping Summertime Experiences: Opportunities to Promote Healthy Development and Well-Being for Children and Youth.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19.
4.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Preventing Reading Difficulties in Young Children.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1998.
5.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Guidance for schools and child care: plan, prepare, and respond to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Accessed July 23, 2020.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community/schools-childcare/guidance-for-schools.html
残酷的COVID-19戏剧性
Katherine C. McKenzie, MD
风城黑鹰译
已六个星期没给妈妈一个拥抱了,话又说回来,自冠状病毒病-19(COVID-19)大流行并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以来,世界各地有数百万的女儿与我一样,可以说同样的话。
妈妈就像我已经照顾了25多年的许多老年患者一样:脆弱,脆弱,但是非常独立并且生活在家里。她之前只住过5次医院:几个女儿的出生和更换主动脉瓣。今年母亲节,我给妈妈打电话时,她却气喘吁吁,说她非常嗜睡。她不能平躺着,也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妈妈以为呼吸急促是因为哮喘加剧,只需要服用一下激素,但是我的一个姐姐住在妈妈附近,姐姐和我都不太确定那是问题所在。我们想让她远离医院;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让她远离COVID-19,我们担心如果让她住医院,可能会导致暴露于Covid-19之下。但是我也很清楚,由于患者们远离医疗机构,因此他们错过了许多严重疾病的诊治机会。
我住在离妈妈150英里外的地方。很明显,妈妈在几个小时内没有好转,我姐姐开车去了妈妈那里,叫了一辆救护车。姐姐戴着口罩和手套,帮助妈妈收拾了一些衣服。紧急医疗救助人员将母亲放在一辆救护车上,并报告妈妈的血氧饱和度为80%。我姐姐被告知不能和妈妈一起上救护车,也不能在急诊室见她。车开走时,姐姐忍不住想,这也许是她最后一次见到母亲了。然后妈妈被救护车送走了。通常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在生病时会轮流坐在病人床边。我们会保持幽默,保持警惕,并为患者和我们自己提供支持。但是妈妈这次是自己一个人病了。患者家人不确定性的感觉和痛苦的情感,交织于最脆弱的孤独感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当救护车离开的那一刹那,似乎妈妈独自一人跌入了深渊。我们曾想象过到达急诊室,面对蒙面和戴手套的医院工作人员,禁止除患者和前线工作人员之外的任何人进入。我们可以哄着还是乞求坐在妈妈旁边?都不会的。
当我在家中听着妈妈在隔着2个州远的急诊室接受检查时,这一切听起来都很耳熟,我给医院送去过数百名这样的患者。漫长的等待,大量的检查, 还有那等了20小时还没有等到床位的感觉。作为医生,我了解。现实就是这样。但是作为一个女儿,至少我仍然想知道为什么我不能在妈妈的身边,与工作人员交谈,提点建议,为妈妈整理一下毯子,因为她总是很冷。取而代之的是,我可怜兮兮地向前台求助,希望听到从护士那儿传递过来的消息,然后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电话。在我妈妈等着轮床时,这距离和同样的的孤独感加剧了疾病始终伴随的内在不确定性。
入院后,需要进行一天的血液检查,利尿和各种监测。然后令人发疯的电话来了:昏迷无反应,心动过缓,低血压,多巴胺输液紧急挂起。接下来,是一系列的问题。我们是否要在心脏导管实验室中为妈妈放置一个临时起搏器,转移到重症监护病房,解除以前确定的的DNR / DNI(不复苏和不插管)愿望?当她的意识减弱时,我勇敢的母亲向床边的医护团队低声说:“我准备好去死了。”但鉴于突然的变化,医疗团队仍然要求我澄清一下,因为我是她的法律代理人。我建议与我的姐妹们进行电话会议,在那儿,我们声音微颤,确认妈妈不希望自己的护理升级了。我需驱车3个小时才能赶到医院,所以我要求继续给她用血管加压药,一位姐姐已经先到医院了。最后,我们能够坐在妈妈病床边了,因为妈妈的治疗管理方式已经改为仅舒适护理。最后一刻,说再见。妈妈快离开我们了,但最后我可以抱住她,因为在“ COVID-19时代”,正如我们现在经常说的那样,只有在死亡临近时,家人才能见上病人一面。
当我姐姐和我聚在妈妈的房间里,其他家人用通电话方式加入时,我们联系了医院的牧师来主管最后的仪式。我的天主教信仰已经不是那么认真,但根深蒂固,但我的母亲仍然是一个信徒,她希望看到牧师庄严地手持一本祈祷书,以一种其他仪式无法保证的方式,在生命的尽头使我们心安。我们和妈妈坐在一起等候时着等他的到来,但是不久我们就意识到他也不会来了。相反,电话响了。COVID-19颠覆的一切:牧师只能在电话里做仪式。如果我可以像过去6周那样通过电话控制病人的高血压,为什么我们不能在电话会议上祈祷?它奏效了:电话里发出了永恒的安慰之词,我姐姐代表牧师对我们母亲的额头实行神职礼。
他结束讲话时,房间里传递一种和平安宁的感觉。血管升压药停止了,我们关了灯,在等待的时候房间变得越来越安静。到这个时候,妈妈已经对COVID-19进行了两次阴性测试。那天晚上我在她的病床与妈妈一起睡觉,这是几周以来的第一次。我知道她不会感染我。由于她要去天国了,所以我不在乎我对她的冒险(传染给妈妈)。
但是妈妈没有死,她睡得很香。尽管是舒适治疗,但第二天早上她的生命体征显示出明显的改善。尽管还不完全正常,但她整夜已经稳定下来。最初被认为是败血症或另一种心肌梗塞的原因可能是迷走神经发作,并伴有一些血容量不足。经过更多讨论,我们决定重新开始她前一天接受的非重症监护,并暂停舒适措施的要求。
看到她病情在改善,我们非常感恩。但是残酷的COVID-19讽刺再次证明病毒本身。既然现在她越来越好了,我们再次离开了妈妈身边。她再次独自一人,努力奋斗,但还活着。
妈妈回到家中了,每天都在改善,每天仍要与她已有的慢性病作斗争,但与我们所有人一样,在可预见的将来,COVID-19仍会给她带来威胁。我们打电话给她,让她患上严重但可以治愈的疾病时去医院,当然要冒感染COVID-19的危险,但会问在她上救护车之前是否应该接受治疗。在与大流行有关的残酷折磨中,还有很多,最具有戏剧性意味的是,我与妈妈亲近的唯一时候竟然是是当我们差点失去她的时候。我们渴望与亲人(许多是最脆弱的)亲近拥抱,但他们必须像他们的生活一样-保持社交距离。因为他们当然会这样做。
A Piece of My Mind
June 30, 2020
A Cruel COVID-19 Irony
Katherine C. McKenzie, MD1
Author Affiliations Article Information
JAMA. Published online June 30, 2020. doi:10.1001/jama.2020.11882
I hadn’t hugged Mom for 6 weeks. But then again, there were millions of daughters around the world who could say the same since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consumed and changed our lives.
Mom was like so many older patients I’ve taken care of for more than 25 years: frail, vulnerable, but fiercely independent and living at home. She’d been hospitalized only 5 times before: to deliver her daughters and for an aortic valve replacement. When I called her on Mother’s Day this year, she was short of breath and said she had slept terribly. She couldn’t lie flat or speak in full sentences. Mom thought her shortness of breath was an asthma exacerbation, and she only needed a course of steroids, but one of my sisters, who lives nearby, and I weren’t so sure. We wanted to keep her out of the hospital; we’d kept her away from COVID-19 so far and were worried about exposure if we brought her in. But I was well aware that many serious illnesses were being missed as patients stayed away from medical settings.
I live 150 miles away, but when it became clear that Mom was not getting better over a few hours, my sister drove to her house and called an ambulance. Donning a mask and gloves, she helped Mom pack some clothes. The emergency medical technicians put our mother in an ambulance and reported an oxygenation saturation of 80% on room air. My sister couldn’t join Mom in the ambulance or meet her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As it drove off, she couldn’t help but think it might be the last time she saw her. And then Mom was gone. In normal times, we’re a family who takes turns sitting at the bedside when someone is sick. We keep a mostly humorous vigil and prop the patient and ourselves up. But Mom was being sent into illness by herself. The typical uncertainty and anguish of an ill family member was compounded by a most vulnerable aloneness.
When the ambulance pulled away, it seemed she was going into the abyss without us. We envisioned arriving at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and confronting masked and gloved hospital staff forbidding anyone but patients and frontline workers from entering. Could we cajole or beg to sit next to Mom? It wouldn’t happen.
As I heard about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workup from my home 2 states away, it sounded familiar, from the hundreds of patients I’ve sent in. A long wait, a lot of tests, no bed available for 20 hours. As a physician, I understood. It’s the way it is. But as a daughter I still wondered why I couldn’t at least be by her side, to talk to the staff, to advocate, to adjust her blanket because she is always cold. Instead, I plaintively appealed to the clerk for word from the nursing staff and waited anxiously for a call. The inherent uncertainty that always accompanies illness was magnified by distance and vicarious loneliness as my mother waited on a gurney.
After being admitted, a day of bloodwork, diuresis, and monitoring unfolded. Then a frantic call came: unresponsiveness, bradycardia, hypotension, dopamine urgently hung. And next, a fusillade of questions. Did we want a temporary pacer placed in the cardiac catheter lab, transfer to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lifting of the DNR/DNI (do not resuscitate and do not intubate) order that was in place? As her consciousness ebbed, my brave mother mumbled to the bedside team, “I’m ready to die,” but they still requested immediate clarity from me, her medical power of attorney, given the sudden change. I appealed for a moment for a conference call with my sisters, where, with pressured speech, we confirmed that she did not want care escalated. I appealed for the vasopressors to continue on the floor while I drove 3 hours to the hospital, where one sister already had arrived. Finally, I was able to sit with Mom because her management had been changed to comfort care only. One last moment to say goodbye. Mom was dying, but finally I could hold her because in the “COVID-19-era,” as we all say so often now, family can join the patient only when death is near.
As my sister and I gathered in Mom’s room, and other family members joined on the phone, we reached out to the hospital priest to administer last rites. My Catholicism is lapsed but deep-rooted, but my mom remains a believer, and the sight of the solemn man in the clerical collar, carrying a book of prayers, reassures us at the end of life in a way no other ritual can. We waited for him to walk through the door as we sat with Mom, but it soon dawned on us that he wouldn’t be coming either. Instead, the phone rang. Another convention upended by COVID-19: telephonic last rites were given. If I could manage hypertension over the phone, as I had been doing for 6 weeks, why couldn’t we pray on a conference call? It worked: the timeless words of reassurance given, with my sister administering divine unction on our mother’s forehead on the priest’s behalf.
A sense of peace descended in the room when he finished. The vasopressors were stopped, and we turned off the lights, growing quiet while we waited. By this time, Mom had tested negative for COVID-19 twice. I got in bed with her that night and held her for the first time in weeks. I knew she wouldn’t infect me. Since she was dying, I didn’t care about my risk to her.
But Mom didn’t die. She slept soundly. Despite comfort care orders, the next morning her vital signs were taken, showing remarkable improvement. Although not normal, she had stabilized overnight. What was initially thought to be sepsis or another myocardial infarction likely was a vagal episode superimposed on some hypovolemia. After more discussions, we decided to restart the noncritical care she had been receiving the day before and suspend comfort-only measures.
How grateful we were that she lived and that she was improving. But the cruel COVID-19 irony declared itself again. Now that she was getting better, we were once again banished from her side. She was alone again, fighting hard, but alive.
Mom is back home, gaining strength every day—battling her chronic illnesses, but like all of us, still menaced by COVID-19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We made the call to bring her in for a serious but treatable illness while risking infection with COVID-19 but questioned whether we should have until she was placed in the ambulance. Of the cruelties associated with the pandemic, and there are many, the most ironic was that the only way I could be close to Mom was when we almost lost her. We are starved for physical contact with our loved ones, many of the most vulnerable, who must distance like their lives depend upon it. Because of course they just might.
Section Editor: Preeti Malani, MD, MSJ, Associate Editor.
Corresponding Author: Katherine C. McKenzie, MD, Yale Center for Asylum Medicine,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367 Cedar St, Yale School of Medicine, New Haven, CT 06510 (katherine.mckenzie@yale.edu).
Published Online: June 30, 2020. doi:10.1001/jama.2020.11882
Conflict of Interest Disclosures: None reported.
Additional Contributions: I thank my mother for allowing me to share this story.
芝加哥的COVID-19病毒株与武汉类似
COVID-19大流行的趋势:从过去看未来
(一)前言
根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中国学者学术论文报道,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冠状病毒-2(SARS-CoV-2)(引起COVID-19的病毒, 网络又称新冠病毒)于2019年12月8日在中国武汉首例出现。那时即使是最有经验的国际公共卫生专家都不能预料它将会迅速地在全球蔓延,会造成这样一个100多年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笔者当时认为病毒可能会传播至他国如美国,但沒预见到当今如此严重的全球性大流行。
2020年1月,一些公共卫生官员开始拉响警报,但直到2020年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才宣布Covid-19全球大流行。
Covid-19的病毒着实把全球各国弄得措手不及,而且人们对其未来发展情况仍然是高度地不可预测,也没有清楚的知识去指导如何去最终地控制这个大流行。
其他两种动物传人的冠状病毒病如SARS(莎士,非典,即由SARS-CoV-1病毒引起的一种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和中东呼吸综合征的冠状病毒[MERS-CoV]的流行病学与SARS-CoV-2有很大的不同;因此,这两种病原体无法为Covid-19提供有用的模型来预测新冠这种大流行预期的结果。
专家认为(The CIDRAP 报告)最好的用来比较的模型是大流行流感。自1700年代初期以来,全球至少已经发生过八次流感大流行,其中四起发生于20世纪(1918-1919、1957、1968)和本世纪2009-2010。当我们试图预测未来情景时,我们可以也必须从过去的流感大流行中学习从而认识当今的COVID-19大流行。通过将COVID-19和流感大流行进行比较,可以帮助我们来预想当前COVID-19大流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N种情况。
目前很多模式主要聚焦在北半球,但是类似的模式也可能发生在南半球。由于南半球缺乏健全的医疗基础设施(包括缺乏足够的医疗设施,个人防护装备)和合并其他疾病,例如其他感染(例如HIV,TB,疟疾),营养不良,南半球某些地区的慢性呼吸道疾病甚至可能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大流行。
(二)Covid-19 和流感大流行的流行病学异同
两者的相似处:
即使冠状病毒与流感病毒从许多方面来说都大不相同,然而COVID-19大流行和流感大流行也有几个重要的相似之处。
首先,SARS-CoV-2和大流行性流感病毒均是新型病毒病原体,全球人口在流行时对这些病毒几乎没有免疫力,从而导致全球人类对病毒的极度敏感性。
其次,SARS-CoV-2和流感病毒均主要通过呼吸道大液滴传播,而且两者均还有较小部分通过气溶胶传播。
第三,两种病毒也都存在无症状传播,从而促进了传播。
最后,两种病毒均能够感染数以百万计的人,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地流行传播。
两者的重要区别:
首先,是潜伏期的不同; 流感的平均潜伏期为2天(范围为1至4天);而COVID-19的平均潜伏期为5天(范围,2至14天)。COVID-19的潜伏期较长,使得病毒可以在被发现之前已经在的不同人群中悄悄地传播。这促成了各国政府在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之前的那种不屑一顾的自满情绪。
其次,这个重要不同因素是无症状感染部分。虽然确切信息仍然在收集中,公共卫生官员表示 25%的COVID-19病例可能是无症状的,不久更好的血清学研究可能会将此百分比向上调高。许多研究已经探索了无症状的流感。一个综述文献发现了一个无症状流感传播者的平均值为16%(范围为4%至28%)。因此,尽管两种病毒都可以导致无症状感染,但COVID-19的无症状分数似乎比流感要高。
第三,这个考虑因素是病人症状发生前病毒传播的时间框架。最近一研究发现,SARS-CoV-2病毒载量在症状发作时最高,表明病毒传播,可能在症状发生之前达到峰值,导致大量的症状前传播。对疗养院居民中SARS-CoV-2的点普遍性研究表明,27名居民测试时无症状,中位4天后24名出现症状(3至5天),支持症状前病毒传播的可能性。对于H1N1大流行性甲型流感病毒,一项研究表明,病毒性传播在症状出现后的第一到第二天达到峰值,也支持流感大流行的病毒症状前传染性不及SARS-Cov-2。
以上所有因素均有助于病毒的传播。
|
|
量化病毒传播能力的一种方法是确定该病毒的基本繁殖数(Basic reproductive number, R0)。R0是单个感染者在完全易感人群中导致新感染人数的平均数量。
R0可能会因以下因素而改变:
影响人与人之间的接触率,例如身体疏远策略和禁足居家令,旨在将R0降低到小于1。当R0低于1时,表明传染爆发是在缩小而不是扩大,因为每个感染者随后感染了少于1个他人。
虽然R0不受群体免疫力的影响(即对病毒免疫的人口比例,这种群体免疫或由自然感染或疫苗接种免疫产生),但是在人口中免疫力可以影响有效繁殖数(effective reproductive number, RE),RE与R0类似,只是RE不依赖于拥有完全易感人群的信息。
人群中的免疫力可以通过将RE降低到1以下而有效地减少或消除传染的爆发。
SARS-CoV-2 中国流行初期的R0估计为2.0至2.5。但是,各个地理区域 的SARS-CoV-2的R0很难得到准确确定,因为识别和测试感染者的能力很受挑战,一项研究表明,其数值可能会是更高,有人认为达到了5。另外,对于SARS-CoV-2,每个人的R0都不相同;它可以因受感染者病毒传播的自然变异性而改变。甚至R0的平均值也不是纯生物量-它取决于行为和接触方式。例如,有人推测在人口稠密或接触频繁的地区(例如大城市),SARS-CoV-2的R0可能更高。
此外,一些证据表明某些人是“超级传播者”,就像在MERS-CoV和
SARS。一些国家通过缓解措施似乎已经能够为将SARS-CoV-2的R0降到低于1,然而随着缓解措施的取消,任何给定区域中的R0可能又会爬回1以上,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导致疾病复发。
大流行性流感的R0因大流行而异,但估计一直在2左右或以下,这表明即使是过去的严重流感大流行病毒也比SARS-CoV-2的传播性小。
一个在2009-10年大流行之后发表的评论文章对报告R0值的最新研究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四个流感大流行。尽管结果有所不同,但最高的中位数R0与1918年和1968年的流感大流行(均为1.8),其次是1957年的大流行(1.65),然后是2009-10年的大流行(1.46)。相比之下,季节性流感大流行的中位数R0为1.27。
(三)以往流感大流行的主要教训
自1700年代初以来发生的八次主要流行病中,大多数流行没有明显的季节性模式。
各个地理区域中,北半球的冬季有两次,春季的三次,夏季的一次,秋季的两次。
七次有早期高峰,然后在几个月内就消失了,没有大量的人群涉及。随后,这七个峰中的每一个在第一次峰后约6个月都有第二次实质性高峰出现。在最初的流行之后的两年内,一些流行病显示出较小的流行病例。
唯一的1968年的大流行开始于更传统的流感样季节性流行,在北半球出现了一个深秋/冬季波,第二个冬天又是第二波。在某些地区,特别是在欧洲,与大流行相关的死亡率第二年更高。
除了2009-2010年那次大流行外,这些大流行的过程并未受到疫苗接种运动的实质性影响,在此期间大约在大流行的开始6个月后美国才开始使用疫苗,直到大流行之后在美国大部分地区达到顶峰时,才可获得大量疫苗。
一份报告估计,在美国,通过疫苗接种计划,预防了70万到1百50万临床病例,4千到1万例住院和200到500例死亡。
自1900年以来发生了三场大流行之后,甲型流感大流行逐渐变得更适合人类,并取代了主要的季节性传播的流感病毒,成了每年鉴定出主要的季节性甲型流感毒株。在2009-2010年大流行之后,大流行性流感H1N1菌株与甲型H3N2流感在季节性上两者共同传播。
观察过去流感大流行的流行病学的关键点,可借鉴并预测COVID-19大流行可能会有以下可能性:
首先,大流行的持续时间可能为18到24个月,因为群体免疫需时间逐渐达到。据有限的血清监测,表明群体将需要时间,迄今可获得的数据表明,人群中只有一小部分受到感染,且感染率因地区而异。鉴于SARS-CoV-2的可传播性,需要60%-70%人群获取免疫以达到群体免疫的关键阈值才能阻止大流行。
由于我们尚不知道对天然SARS-CoV-2的免疫力持续时间,这可能会使情况变得复杂(可能短至几个月或长达几年)。根据季节性冠状病毒,我们可以预见,即使暴露后免疫力随时间下降,仍然可能会有一定降低疾病严重程度和降低传染性这种保护作用,当然这对于SARS-CoV-2仍有待评估。
大流行过程也可能受到疫苗的影响;但是,直到至少要等到2021年的某个时候,最快也要今年底。我们不知道在疫苗开发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这可能会延迟时间表。
其次,COVID-19大流行的未来存在几种不同的情况,其中一些是与过去的流感大流行期间发生的情况一致。这些可以总结如下,分别是三种可能的情景,如下图所示(横轴是时间, 纵轴是病例数):
情景1:2020年春季的COVID-19是第一波,随后是一系列发生在整个夏季重复的较小波,然后持续1-2年,并在2021年消失。这些波的发生与地区,缓解措施,以及如何解除缓解的方法有关。如果是这种情景,那么在接下来的1至2年里,根据波峰的高度,这种情况可能需要定期恢复缓解措施,并且随后放宽这些缓解措接。
情景2:2020年春季第一波COVID-19,之后是秋天或冬天的大波,和随后的一个或多个较小波,这种模式需要在2021年秋季时恢复采取缓解措施,以期降低感染传播,预防医疗保健系统挤兑。这种模式与1918-19年大流行相似。在那次大流行中,开始于1918年3月时有一小波,小波于夏季消停了几个月。然后在1918年秋天,冬季,1919年春天出现一个更大的峰值。1919年的那个波,标志着大流行病的终结。
1957-58年大流行遵循类似的模式,但规模较小,始于春季浪潮,随后是更大的秋季浪潮,连续的小波浪,持续发生了数年。
2009-10年大流行也遵循了始于春季的模式,在春季波之后是更大的下降波。
情景3:2020年春季的第一波COVID-19浪潮之后,持续的“缓慢燃烧”地传播和不停有新病例的发生,但没有清晰的波形。同样,此模式可能会有所不同,在地理上可能会受到各个地区所采取的缓解措施程度的影响。
而在过去的流感大流行中没有发现这第三种模式,它仍然有可能发生在COVID-19流行上。这第三种情况可能不需要恢复缓解措施,尽管案例和死亡仍将继续发生。
无论大流行发生在哪种情况下(假设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持续实施缓解措施),我们必须为至少18至24个月的重要COVID-19活动做好准备,并出现热点定期在不同的地理区域内。随着大流行的减弱,SARS-CoV-2很可能会继续会在人群中传播,并将与季节性模式同步,严重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与其他病原性较低的冠状病毒一样,例如β冠状病毒OC43和HKU1(Kissler 2020)和过去的大流行性流感病毒都是这样的。
在年初,笔者曾认为covid-19与莎士一样,会在夏天来临的时候消失,看来这对covid-19影响是低估了,这种在夏天突然消失不再重来的可能性较小,我们必须准备更可能的1-2年疫情反反复复。大家不要为谁对谁错甩来甩去,这影响了全球近两百个国家地区的大流行,怎么可能是哪一人哪一国的失误呢?反过来说,人们又为什么不从中找出问题的关键所在以避免再次发生呢?
|
|
残酷的COVID-19戏剧性
Katherine C. McKenzie, MD
风城黑鹰译
已六个星期没给妈妈一个拥抱了,话又说回来,自冠状病毒病-19(COVID-19)大流行并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以来,世界各地有数百万的女儿与我一样,可以说同样的话。
妈妈就像我已经照顾了25多年的许多老年患者一样:脆弱,脆弱,但是非常独立并且生活在家里。她之前只住过5次医院:几个女儿的出生和更换主动脉瓣。今年母亲节,我给妈妈打电话时,她却气喘吁吁,说她非常嗜睡。她不能平躺着,也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妈妈以为呼吸急促是因为哮喘加剧,只需要服用一下激素,但是我的一个姐姐住在妈妈附近,姐姐和我都不太确定那是问题所在。我们想让她远离医院;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让她远离COVID-19,我们担心如果让她住医院,可能会导致暴露于Covid-19之下。但是我也很清楚,由于患者们远离医疗机构,因此他们错过了许多严重疾病的诊治机会。
我住在离妈妈150英里外的地方。很明显,妈妈在几个小时内没有好转,我姐姐开车去了妈妈那里,叫了一辆救护车。姐姐戴着口罩和手套,帮助妈妈收拾了一些衣服。紧急医疗救助人员将母亲放在一辆救护车上,并报告妈妈的血氧饱和度为80%。我姐姐被告知不能和妈妈一起上救护车,也不能在急诊室见她。车开走时,姐姐忍不住想,这也许是她最后一次见到母亲了。然后妈妈被救护车送走了。通常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在生病时会轮流坐在病人床边。我们会保持幽默,保持警惕,并为患者和我们自己提供支持。但是妈妈这次是自己一个人病了。患者家人不确定性的感觉和痛苦的情感,交织于最脆弱的孤独感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当救护车离开的那一刹那,似乎妈妈独自一人跌入了深渊。我们曾想象过到达急诊室,面对蒙面和戴手套的医院工作人员,禁止除患者和前线工作人员之外的任何人进入。我们可以哄着还是乞求坐在妈妈旁边?都不会的。
当我在家中听着妈妈在隔着2个州远的急诊室接受检查时,这一切听起来都很耳熟,我给医院送去过数百名这样的患者。漫长的等待,大量的检查, 还有那等了20小时还没有等到床位的感觉。作为医生,我了解。现实就是这样。但是作为一个女儿,至少我仍然想知道为什么我不能在妈妈的身边,与工作人员交谈,提点建议,为妈妈整理一下毯子,因为她总是很冷。取而代之的是,我可怜兮兮地向前台求助,希望听到从护士那儿传递过来的消息,然后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电话。在我妈妈等着轮床时,这距离和同样的的孤独感加剧了疾病始终伴随的内在不确定性。
入院后,需要进行一天的血液检查,利尿和各种监测。然后令人发疯的电话来了:昏迷无反应,心动过缓,低血压,多巴胺输液紧急挂起。接下来,是一系列的问题。我们是否要在心脏导管实验室中为妈妈放置一个临时起搏器,转移到重症监护病房,解除以前确定的的DNR / DNI(不复苏和不插管)愿望?当她的意识减弱时,我勇敢的母亲向床边的医护团队低声说:“我准备好去死了。”但鉴于突然的变化,医疗团队仍然要求我澄清一下,因为我是她的法律代理人。我建议与我的姐妹们进行电话会议,在那儿,我们声音微颤,确认妈妈不希望自己的护理升级了。我需驱车3个小时才能赶到医院,所以我要求继续给她用血管加压药,一位姐姐已经先到医院了。最后,我们能够坐在妈妈病床边了,因为妈妈的治疗管理方式已经改为仅舒适护理。最后一刻,说再见。妈妈快离开我们了,但最后我可以抱住她,因为在“ COVID-19时代”,正如我们现在经常说的那样,只有在死亡临近时,家人才能见上病人一面。
当我姐姐和我聚在妈妈的房间里,其他家人用通电话方式加入时,我们联系了医院的牧师来主管最后的仪式。我的天主教信仰已经不是那么认真,但根深蒂固,但我的母亲仍然是一个信徒,她希望看到牧师庄严地手持一本祈祷书,以一种其他仪式无法保证的方式,在生命的尽头使我们心安。我们和妈妈坐在一起等候时着等他的到来,但是不久我们就意识到他也不会来了。相反,电话响了。COVID-19颠覆的一切:牧师只能在电话里做仪式。如果我可以像过去6周那样通过电话控制病人的高血压,为什么我们不能在电话会议上祈祷?它奏效了:电话里发出了永恒的安慰之词,我姐姐代表牧师对我们母亲的额头实行神职礼。
他结束讲话时,房间里传递一种和平安宁的感觉。血管升压药停止了,我们关了灯,在等待的时候房间变得越来越安静。到这个时候,妈妈已经对COVID-19进行了两次阴性测试。那天晚上我在她的病床与妈妈一起睡觉,这是几周以来的第一次。我知道她不会感染我。由于她要去天国了,所以我不在乎我对她的冒险(传染给妈妈)。
但是妈妈没有死,她睡得很香。尽管是舒适治疗,但第二天早上她的生命体征显示出明显的改善。尽管还不完全正常,但她整夜已经稳定下来。最初被认为是败血症或另一种心肌梗塞的原因可能是迷走神经发作,并伴有一些血容量不足。经过更多讨论,我们决定重新开始她前一天接受的非重症监护,并暂停舒适措施的要求。
看到她病情在改善,我们非常感恩。但是残酷的COVID-19讽刺再次证明病毒本身。既然现在她越来越好了,我们再次离开了妈妈身边。她再次独自一人,努力奋斗,但还活着。
妈妈回到家中了,每天都在改善,每天仍要与她已有的慢性病作斗争,但与我们所有人一样,在可预见的将来,COVID-19仍会给她带来威胁。我们打电话给她,让她患上严重但可以治愈的疾病时去医院,当然要冒感染COVID-19的危险,但会问在她上救护车之前是否应该接受治疗。在与大流行有关的残酷折磨中,还有很多,最具有戏剧性意味的是,我与妈妈亲近的唯一时候竟然是是当我们差点失去她的时候。我们渴望与亲人(许多是最脆弱的)亲近拥抱,但他们必须像他们的生活一样-保持社交距离。因为他们当然会这样做。
A Piece of My Mind
June 30, 2020
A Cruel COVID-19 Irony
Katherine C. McKenzie, MD1
Author Affiliations Article Information
JAMA. Published online June 30, 2020. doi:10.1001/jama.2020.11882
I hadn’t hugged Mom for 6 weeks. But then again, there were millions of daughters around the world who could say the same since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consumed and changed our lives.
Mom was like so many older patients I’ve taken care of for more than 25 years: frail, vulnerable, but fiercely independent and living at home. She’d been hospitalized only 5 times before: to deliver her daughters and for an aortic valve replacement. When I called her on Mother’s Day this year, she was short of breath and said she had slept terribly. She couldn’t lie flat or speak in full sentences. Mom thought her shortness of breath was an asthma exacerbation, and she only needed a course of steroids, but one of my sisters, who lives nearby, and I weren’t so sure. We wanted to keep her out of the hospital; we’d kept her away from COVID-19 so far and were worried about exposure if we brought her in. But I was well aware that many serious illnesses were being missed as patients stayed away from medical settings.
I live 150 miles away, but when it became clear that Mom was not getting better over a few hours, my sister drove to her house and called an ambulance. Donning a mask and gloves, she helped Mom pack some clothes. The emergency medical technicians put our mother in an ambulance and reported an oxygenation saturation of 80% on room air. My sister couldn’t join Mom in the ambulance or meet her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As it drove off, she couldn’t help but think it might be the last time she saw her. And then Mom was gone. In normal times, we’re a family who takes turns sitting at the bedside when someone is sick. We keep a mostly humorous vigil and prop the patient and ourselves up. But Mom was being sent into illness by herself. The typical uncertainty and anguish of an ill family member was compounded by a most vulnerable aloneness.
When the ambulance pulled away, it seemed she was going into the abyss without us. We envisioned arriving at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and confronting masked and gloved hospital staff forbidding anyone but patients and frontline workers from entering. Could we cajole or beg to sit next to Mom? It wouldn’t happen.
As I heard about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workup from my home 2 states away, it sounded familiar, from the hundreds of patients I’ve sent in. A long wait, a lot of tests, no bed available for 20 hours. As a physician, I understood. It’s the way it is. But as a daughter I still wondered why I couldn’t at least be by her side, to talk to the staff, to advocate, to adjust her blanket because she is always cold. Instead, I plaintively appealed to the clerk for word from the nursing staff and waited anxiously for a call. The inherent uncertainty that always accompanies illness was magnified by distance and vicarious loneliness as my mother waited on a gurney.
After being admitted, a day of bloodwork, diuresis, and monitoring unfolded. Then a frantic call came: unresponsiveness, bradycardia, hypotension, dopamine urgently hung. And next, a fusillade of questions. Did we want a temporary pacer placed in the cardiac catheter lab, transfer to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lifting of the DNR/DNI (do not resuscitate and do not intubate) order that was in place? As her consciousness ebbed, my brave mother mumbled to the bedside team, “I’m ready to die,” but they still requested immediate clarity from me, her medical power of attorney, given the sudden change. I appealed for a moment for a conference call with my sisters, where, with pressured speech, we confirmed that she did not want care escalated. I appealed for the vasopressors to continue on the floor while I drove 3 hours to the hospital, where one sister already had arrived. Finally, I was able to sit with Mom because her management had been changed to comfort care only. One last moment to say goodbye. Mom was dying, but finally I could hold her because in the “COVID-19-era,” as we all say so often now, family can join the patient only when death is near.
As my sister and I gathered in Mom’s room, and other family members joined on the phone, we reached out to the hospital priest to administer last rites. My Catholicism is lapsed but deep-rooted, but my mom remains a believer, and the sight of the solemn man in the clerical collar, carrying a book of prayers, reassures us at the end of life in a way no other ritual can. We waited for him to walk through the door as we sat with Mom, but it soon dawned on us that he wouldn’t be coming either. Instead, the phone rang. Another convention upended by COVID-19: telephonic last rites were given. If I could manage hypertension over the phone, as I had been doing for 6 weeks, why couldn’t we pray on a conference call? It worked: the timeless words of reassurance given, with my sister administering divine unction on our mother’s forehead on the priest’s behalf.
A sense of peace descended in the room when he finished. The vasopressors were stopped, and we turned off the lights, growing quiet while we waited. By this time, Mom had tested negative for COVID-19 twice. I got in bed with her that night and held her for the first time in weeks. I knew she wouldn’t infect me. Since she was dying, I didn’t care about my risk to her.
But Mom didn’t die. She slept soundly. Despite comfort care orders, the next morning her vital signs were taken, showing remarkable improvement. Although not normal, she had stabilized overnight. What was initially thought to be sepsis or another myocardial infarction likely was a vagal episode superimposed on some hypovolemia. After more discussions, we decided to restart the noncritical care she had been receiving the day before and suspend comfort-only measures.
How grateful we were that she lived and that she was improving. But the cruel COVID-19 irony declared itself again. Now that she was getting better, we were once again banished from her side. She was alone again, fighting hard, but alive.
Mom is back home, gaining strength every day—battling her chronic illnesses, but like all of us, still menaced by COVID-19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We made the call to bring her in for a serious but treatable illness while risking infection with COVID-19 but questioned whether we should have until she was placed in the ambulance. Of the cruelties associated with the pandemic, and there are many, the most ironic was that the only way I could be close to Mom was when we almost lost her. We are starved for physical contact with our loved ones, many of the most vulnerable, who must distance like their lives depend upon it. Because of course they just might.
Section Editor: Preeti Malani, MD, MSJ, Associate Editor.
Corresponding Author: Katherine C. McKenzie, MD, Yale Center for Asylum Medicine,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367 Cedar St, Yale School of Medicine, New Haven, CT 06510 (katherine.mckenzie@yale.edu).
Published Online: June 30, 2020. doi:10.1001/jama.2020.11882
Conflict of Interest Disclosures: None reported.
Additional Contributions: I thank my mother for allowing me to share this story.
芝加哥的COVID-19病毒株与武汉类似
COVID-19大流行的趋势:从过去看未来
(一)前言
根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中国学者学术论文报道,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冠状病毒-2(SARS-CoV-2)(引起COVID-19的病毒, 网络又称新冠病毒)于2019年12月8日在中国武汉首例出现。那时即使是最有经验的国际公共卫生专家都不能预料它将会迅速地在全球蔓延,会造成这样一个100多年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笔者当时认为病毒可能会传播至他国如美国,但沒预见到当今如此严重的全球性大流行。
2020年1月,一些公共卫生官员开始拉响警报,但直到2020年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才宣布Covid-19全球大流行。
Covid-19的病毒着实把全球各国弄得措手不及,而且人们对其未来发展情况仍然是高度地不可预测,也没有清楚的知识去指导如何去最终地控制这个大流行。
其他两种动物传人的冠状病毒病如SARS(莎士,非典,即由SARS-CoV-1病毒引起的一种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和中东呼吸综合征的冠状病毒[MERS-CoV]的流行病学与SARS-CoV-2有很大的不同;因此,这两种病原体无法为Covid-19提供有用的模型来预测新冠这种大流行预期的结果。
专家认为(The CIDRAP 报告)最好的用来比较的模型是大流行流感。自1700年代初期以来,全球至少已经发生过八次流感大流行,其中四起发生于20世纪(1918-1919、1957、1968)和本世纪2009-2010。当我们试图预测未来情景时,我们可以也必须从过去的流感大流行中学习从而认识当今的COVID-19大流行。通过将COVID-19和流感大流行进行比较,可以帮助我们来预想当前COVID-19大流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N种情况。
目前很多模式主要聚焦在北半球,但是类似的模式也可能发生在南半球。由于南半球缺乏健全的医疗基础设施(包括缺乏足够的医疗设施,个人防护装备)和合并其他疾病,例如其他感染(例如HIV,TB,疟疾),营养不良,南半球某些地区的慢性呼吸道疾病甚至可能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大流行。
(二)Covid-19 和流感大流行的流行病学异同
两者的相似处:
即使冠状病毒与流感病毒从许多方面来说都大不相同,然而COVID-19大流行和流感大流行也有几个重要的相似之处。
首先,SARS-CoV-2和大流行性流感病毒均是新型病毒病原体,全球人口在流行时对这些病毒几乎没有免疫力,从而导致全球人类对病毒的极度敏感性。
其次,SARS-CoV-2和流感病毒均主要通过呼吸道大液滴传播,而且两者均还有较小部分通过气溶胶传播。
第三,两种病毒也都存在无症状传播,从而促进了传播。
最后,两种病毒均能够感染数以百万计的人,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地流行传播。
两者的重要区别:
首先,是潜伏期的不同; 流感的平均潜伏期为2天(范围为1至4天);而COVID-19的平均潜伏期为5天(范围,2至14天)。COVID-19的潜伏期较长,使得病毒可以在被发现之前已经在的不同人群中悄悄地传播。这促成了各国政府在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之前的那种不屑一顾的自满情绪。
其次,这个重要不同因素是无症状感染部分。虽然确切信息仍然在收集中,公共卫生官员表示 25%的COVID-19病例可能是无症状的,不久更好的血清学研究可能会将此百分比向上调高。许多研究已经探索了无症状的流感。一个综述文献发现了一个无症状流感传播者的平均值为16%(范围为4%至28%)。因此,尽管两种病毒都可以导致无症状感染,但COVID-19的无症状分数似乎比流感要高。
第三,这个考虑因素是病人症状发生前病毒传播的时间框架。最近一研究发现,SARS-CoV-2病毒载量在症状发作时最高,表明病毒传播,可能在症状发生之前达到峰值,导致大量的症状前传播。对疗养院居民中SARS-CoV-2的点普遍性研究表明,27名居民测试时无症状,中位4天后24名出现症状(3至5天),支持症状前病毒传播的可能性。对于H1N1大流行性甲型流感病毒,一项研究表明,病毒性传播在症状出现后的第一到第二天达到峰值,也支持流感大流行的病毒症状前传染性不及SARS-Cov-2。
以上所有因素均有助于病毒的传播。
|
|
量化病毒传播能力的一种方法是确定该病毒的基本繁殖数(Basic reproductive number, R0)。R0是单个感染者在完全易感人群中导致新感染人数的平均数量。
R0可能会因以下因素而改变:
影响人与人之间的接触率,例如身体疏远策略和禁足居家令,旨在将R0降低到小于1。当R0低于1时,表明传染爆发是在缩小而不是扩大,因为每个感染者随后感染了少于1个他人。
虽然R0不受群体免疫力的影响(即对病毒免疫的人口比例,这种群体免疫或由自然感染或疫苗接种免疫产生),但是在人口中免疫力可以影响有效繁殖数(effective reproductive number, RE),RE与R0类似,只是RE不依赖于拥有完全易感人群的信息。
人群中的免疫力可以通过将RE降低到1以下而有效地减少或消除传染的爆发。
SARS-CoV-2 中国流行初期的R0估计为2.0至2.5。但是,各个地理区域 的SARS-CoV-2的R0很难得到准确确定,因为识别和测试感染者的能力很受挑战,一项研究表明,其数值可能会是更高,有人认为达到了5。另外,对于SARS-CoV-2,每个人的R0都不相同;它可以因受感染者病毒传播的自然变异性而改变。甚至R0的平均值也不是纯生物量-它取决于行为和接触方式。例如,有人推测在人口稠密或接触频繁的地区(例如大城市),SARS-CoV-2的R0可能更高。
此外,一些证据表明某些人是“超级传播者”,就像在MERS-CoV和
SARS。一些国家通过缓解措施似乎已经能够为将SARS-CoV-2的R0降到低于1,然而随着缓解措施的取消,任何给定区域中的R0可能又会爬回1以上,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导致疾病复发。
大流行性流感的R0因大流行而异,但估计一直在2左右或以下,这表明即使是过去的严重流感大流行病毒也比SARS-CoV-2的传播性小。
一个在2009-10年大流行之后发表的评论文章对报告R0值的最新研究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四个流感大流行。尽管结果有所不同,但最高的中位数R0与1918年和1968年的流感大流行(均为1.8),其次是1957年的大流行(1.65),然后是2009-10年的大流行(1.46)。相比之下,季节性流感大流行的中位数R0为1.27。
(三)以往流感大流行的主要教训
自1700年代初以来发生的八次主要流行病中,大多数流行没有明显的季节性模式。
各个地理区域中,北半球的冬季有两次,春季的三次,夏季的一次,秋季的两次。
七次有早期高峰,然后在几个月内就消失了,没有大量的人群涉及。随后,这七个峰中的每一个在第一次峰后约6个月都有第二次实质性高峰出现。在最初的流行之后的两年内,一些流行病显示出较小的流行病例。
唯一的1968年的大流行开始于更传统的流感样季节性流行,在北半球出现了一个深秋/冬季波,第二个冬天又是第二波。在某些地区,特别是在欧洲,与大流行相关的死亡率第二年更高。
除了2009-2010年那次大流行外,这些大流行的过程并未受到疫苗接种运动的实质性影响,在此期间大约在大流行的开始6个月后美国才开始使用疫苗,直到大流行之后在美国大部分地区达到顶峰时,才可获得大量疫苗。
一份报告估计,在美国,通过疫苗接种计划,预防了70万到1百50万临床病例,4千到1万例住院和200到500例死亡。
自1900年以来发生了三场大流行之后,甲型流感大流行逐渐变得更适合人类,并取代了主要的季节性传播的流感病毒,成了每年鉴定出主要的季节性甲型流感毒株。在2009-2010年大流行之后,大流行性流感H1N1菌株与甲型H3N2流感在季节性上两者共同传播。
观察过去流感大流行的流行病学的关键点,可借鉴并预测COVID-19大流行可能会有以下可能性:
首先,大流行的持续时间可能为18到24个月,因为群体免疫需时间逐渐达到。据有限的血清监测,表明群体将需要时间,迄今可获得的数据表明,人群中只有一小部分受到感染,且感染率因地区而异。鉴于SARS-CoV-2的可传播性,需要60%-70%人群获取免疫以达到群体免疫的关键阈值才能阻止大流行。
由于我们尚不知道对天然SARS-CoV-2的免疫力持续时间,这可能会使情况变得复杂(可能短至几个月或长达几年)。根据季节性冠状病毒,我们可以预见,即使暴露后免疫力随时间下降,仍然可能会有一定降低疾病严重程度和降低传染性这种保护作用,当然这对于SARS-CoV-2仍有待评估。
大流行过程也可能受到疫苗的影响;但是,直到至少要等到2021年的某个时候,最快也要今年底。我们不知道在疫苗开发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这可能会延迟时间表。
其次,COVID-19大流行的未来存在几种不同的情况,其中一些是与过去的流感大流行期间发生的情况一致。这些可以总结如下,分别是三种可能的情景,如下图所示(横轴是时间, 纵轴是病例数):
情景1:2020年春季的COVID-19是第一波,随后是一系列发生在整个夏季重复的较小波,然后持续1-2年,并在2021年消失。这些波的发生与地区,缓解措施,以及如何解除缓解的方法有关。如果是这种情景,那么在接下来的1至2年里,根据波峰的高度,这种情况可能需要定期恢复缓解措施,并且随后放宽这些缓解措接。
情景2:2020年春季第一波COVID-19,之后是秋天或冬天的大波,和随后的一个或多个较小波,这种模式需要在2021年秋季时恢复采取缓解措施,以期降低感染传播,预防医疗保健系统挤兑。这种模式与1918-19年大流行相似。在那次大流行中,开始于1918年3月时有一小波,小波于夏季消停了几个月。然后在1918年秋天,冬季,1919年春天出现一个更大的峰值。1919年的那个波,标志着大流行病的终结。
1957-58年大流行遵循类似的模式,但规模较小,始于春季浪潮,随后是更大的秋季浪潮,连续的小波浪,持续发生了数年。
2009-10年大流行也遵循了始于春季的模式,在春季波之后是更大的下降波。
情景3:2020年春季的第一波COVID-19浪潮之后,持续的“缓慢燃烧”地传播和不停有新病例的发生,但没有清晰的波形。同样,此模式可能会有所不同,在地理上可能会受到各个地区所采取的缓解措施程度的影响。
而在过去的流感大流行中没有发现这第三种模式,它仍然有可能发生在COVID-19流行上。这第三种情况可能不需要恢复缓解措施,尽管案例和死亡仍将继续发生。
无论大流行发生在哪种情况下(假设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持续实施缓解措施),我们必须为至少18至24个月的重要COVID-19活动做好准备,并出现热点定期在不同的地理区域内。随着大流行的减弱,SARS-CoV-2很可能会继续会在人群中传播,并将与季节性模式同步,严重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与其他病原性较低的冠状病毒一样,例如β冠状病毒OC43和HKU1(Kissler 2020)和过去的大流行性流感病毒都是这样的。
在年初,笔者曾认为covid-19与莎士一样,会在夏天来临的时候消失,看来这对covid-19影响是低估了,这种在夏天突然消失不再重来的可能性较小,我们必须准备更可能的1-2年疫情反反复复。大家不要为谁对谁错甩来甩去,这影响了全球近两百个国家地区的大流行,怎么可能是哪一人哪一国的失误呢?反过来说,人们又为什么不从中找出问题的关键所在以避免再次发生呢?
|
|
残酷的COVID-19戏剧性
Katherine C. McKenzie, MD
风城黑鹰译
已六个星期没给妈妈一个拥抱了,话又说回来,自冠状病毒病-19(COVID-19)大流行并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以来,世界各地有数百万的女儿与我一样,可以说同样的话。
妈妈就像我已经照顾了25多年的许多老年患者一样:脆弱,脆弱,但是非常独立并且生活在家里。她之前只住过5次医院:几个女儿的出生和更换主动脉瓣。今年母亲节,我给妈妈打电话时,她却气喘吁吁,说她非常嗜睡。她不能平躺着,也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妈妈以为呼吸急促是因为哮喘加剧,只需要服用一下激素,但是我的一个姐姐住在妈妈附近,姐姐和我都不太确定那是问题所在。我们想让她远离医院;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让她远离COVID-19,我们担心如果让她住医院,可能会导致暴露于Covid-19之下。但是我也很清楚,由于患者们远离医疗机构,因此他们错过了许多严重疾病的诊治机会。
我住在离妈妈150英里外的地方。很明显,妈妈在几个小时内没有好转,我姐姐开车去了妈妈那里,叫了一辆救护车。姐姐戴着口罩和手套,帮助妈妈收拾了一些衣服。紧急医疗救助人员将母亲放在一辆救护车上,并报告妈妈的血氧饱和度为80%。我姐姐被告知不能和妈妈一起上救护车,也不能在急诊室见她。车开走时,姐姐忍不住想,这也许是她最后一次见到母亲了。然后妈妈被救护车送走了。通常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在生病时会轮流坐在病人床边。我们会保持幽默,保持警惕,并为患者和我们自己提供支持。但是妈妈这次是自己一个人病了。患者家人不确定性的感觉和痛苦的情感,交织于最脆弱的孤独感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当救护车离开的那一刹那,似乎妈妈独自一人跌入了深渊。我们曾想象过到达急诊室,面对蒙面和戴手套的医院工作人员,禁止除患者和前线工作人员之外的任何人进入。我们可以哄着还是乞求坐在妈妈旁边?都不会的。
当我在家中听着妈妈在隔着2个州远的急诊室接受检查时,这一切听起来都很耳熟,我给医院送去过数百名这样的患者。漫长的等待,大量的检查, 还有那等了20小时还没有等到床位的感觉。作为医生,我了解。现实就是这样。但是作为一个女儿,至少我仍然想知道为什么我不能在妈妈的身边,与工作人员交谈,提点建议,为妈妈整理一下毯子,因为她总是很冷。取而代之的是,我可怜兮兮地向前台求助,希望听到从护士那儿传递过来的消息,然后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电话。在我妈妈等着轮床时,这距离和同样的的孤独感加剧了疾病始终伴随的内在不确定性。
入院后,需要进行一天的血液检查,利尿和各种监测。然后令人发疯的电话来了:昏迷无反应,心动过缓,低血压,多巴胺输液紧急挂起。接下来,是一系列的问题。我们是否要在心脏导管实验室中为妈妈放置一个临时起搏器,转移到重症监护病房,解除以前确定的的DNR / DNI(不复苏和不插管)愿望?当她的意识减弱时,我勇敢的母亲向床边的医护团队低声说:“我准备好去死了。”但鉴于突然的变化,医疗团队仍然要求我澄清一下,因为我是她的法律代理人。我建议与我的姐妹们进行电话会议,在那儿,我们声音微颤,确认妈妈不希望自己的护理升级了。我需驱车3个小时才能赶到医院,所以我要求继续给她用血管加压药,一位姐姐已经先到医院了。最后,我们能够坐在妈妈病床边了,因为妈妈的治疗管理方式已经改为仅舒适护理。最后一刻,说再见。妈妈快离开我们了,但最后我可以抱住她,因为在“ COVID-19时代”,正如我们现在经常说的那样,只有在死亡临近时,家人才能见上病人一面。
当我姐姐和我聚在妈妈的房间里,其他家人用通电话方式加入时,我们联系了医院的牧师来主管最后的仪式。我的天主教信仰已经不是那么认真,但根深蒂固,但我的母亲仍然是一个信徒,她希望看到牧师庄严地手持一本祈祷书,以一种其他仪式无法保证的方式,在生命的尽头使我们心安。我们和妈妈坐在一起等候时着等他的到来,但是不久我们就意识到他也不会来了。相反,电话响了。COVID-19颠覆的一切:牧师只能在电话里做仪式。如果我可以像过去6周那样通过电话控制病人的高血压,为什么我们不能在电话会议上祈祷?它奏效了:电话里发出了永恒的安慰之词,我姐姐代表牧师对我们母亲的额头实行神职礼。
他结束讲话时,房间里传递一种和平安宁的感觉。血管升压药停止了,我们关了灯,在等待的时候房间变得越来越安静。到这个时候,妈妈已经对COVID-19进行了两次阴性测试。那天晚上我在她的病床与妈妈一起睡觉,这是几周以来的第一次。我知道她不会感染我。由于她要去天国了,所以我不在乎我对她的冒险(传染给妈妈)。
但是妈妈没有死,她睡得很香。尽管是舒适治疗,但第二天早上她的生命体征显示出明显的改善。尽管还不完全正常,但她整夜已经稳定下来。最初被认为是败血症或另一种心肌梗塞的原因可能是迷走神经发作,并伴有一些血容量不足。经过更多讨论,我们决定重新开始她前一天接受的非重症监护,并暂停舒适措施的要求。
看到她病情在改善,我们非常感恩。但是残酷的COVID-19讽刺再次证明病毒本身。既然现在她越来越好了,我们再次离开了妈妈身边。她再次独自一人,努力奋斗,但还活着。
妈妈回到家中了,每天都在改善,每天仍要与她已有的慢性病作斗争,但与我们所有人一样,在可预见的将来,COVID-19仍会给她带来威胁。我们打电话给她,让她患上严重但可以治愈的疾病时去医院,当然要冒感染COVID-19的危险,但会问在她上救护车之前是否应该接受治疗。在与大流行有关的残酷折磨中,还有很多,最具有戏剧性意味的是,我与妈妈亲近的唯一时候竟然是是当我们差点失去她的时候。我们渴望与亲人(许多是最脆弱的)亲近拥抱,但他们必须像他们的生活一样-保持社交距离。因为他们当然会这样做。
A Piece of My Mind
June 30, 2020
A Cruel COVID-19 Irony
Katherine C. McKenzie, MD1
Author Affiliations Article Information
JAMA. Published online June 30, 2020. doi:10.1001/jama.2020.11882
I hadn’t hugged Mom for 6 weeks. But then again, there were millions of daughters around the world who could say the same since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consumed and changed our lives.
Mom was like so many older patients I’ve taken care of for more than 25 years: frail, vulnerable, but fiercely independent and living at home. She’d been hospitalized only 5 times before: to deliver her daughters and for an aortic valve replacement. When I called her on Mother’s Day this year, she was short of breath and said she had slept terribly. She couldn’t lie flat or speak in full sentences. Mom thought her shortness of breath was an asthma exacerbation, and she only needed a course of steroids, but one of my sisters, who lives nearby, and I weren’t so sure. We wanted to keep her out of the hospital; we’d kept her away from COVID-19 so far and were worried about exposure if we brought her in. But I was well aware that many serious illnesses were being missed as patients stayed away from medical settings.
I live 150 miles away, but when it became clear that Mom was not getting better over a few hours, my sister drove to her house and called an ambulance. Donning a mask and gloves, she helped Mom pack some clothes. The emergency medical technicians put our mother in an ambulance and reported an oxygenation saturation of 80% on room air. My sister couldn’t join Mom in the ambulance or meet her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As it drove off, she couldn’t help but think it might be the last time she saw her. And then Mom was gone. In normal times, we’re a family who takes turns sitting at the bedside when someone is sick. We keep a mostly humorous vigil and prop the patient and ourselves up. But Mom was being sent into illness by herself. The typical uncertainty and anguish of an ill family member was compounded by a most vulnerable aloneness.
When the ambulance pulled away, it seemed she was going into the abyss without us. We envisioned arriving at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and confronting masked and gloved hospital staff forbidding anyone but patients and frontline workers from entering. Could we cajole or beg to sit next to Mom? It wouldn’t happen.
As I heard about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workup from my home 2 states away, it sounded familiar, from the hundreds of patients I’ve sent in. A long wait, a lot of tests, no bed available for 20 hours. As a physician, I understood. It’s the way it is. But as a daughter I still wondered why I couldn’t at least be by her side, to talk to the staff, to advocate, to adjust her blanket because she is always cold. Instead, I plaintively appealed to the clerk for word from the nursing staff and waited anxiously for a call. The inherent uncertainty that always accompanies illness was magnified by distance and vicarious loneliness as my mother waited on a gurney.
After being admitted, a day of bloodwork, diuresis, and monitoring unfolded. Then a frantic call came: unresponsiveness, bradycardia, hypotension, dopamine urgently hung. And next, a fusillade of questions. Did we want a temporary pacer placed in the cardiac catheter lab, transfer to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lifting of the DNR/DNI (do not resuscitate and do not intubate) order that was in place? As her consciousness ebbed, my brave mother mumbled to the bedside team, “I’m ready to die,” but they still requested immediate clarity from me, her medical power of attorney, given the sudden change. I appealed for a moment for a conference call with my sisters, where, with pressured speech, we confirmed that she did not want care escalated. I appealed for the vasopressors to continue on the floor while I drove 3 hours to the hospital, where one sister already had arrived. Finally, I was able to sit with Mom because her management had been changed to comfort care only. One last moment to say goodbye. Mom was dying, but finally I could hold her because in the “COVID-19-era,” as we all say so often now, family can join the patient only when death is near.
As my sister and I gathered in Mom’s room, and other family members joined on the phone, we reached out to the hospital priest to administer last rites. My Catholicism is lapsed but deep-rooted, but my mom remains a believer, and the sight of the solemn man in the clerical collar, carrying a book of prayers, reassures us at the end of life in a way no other ritual can. We waited for him to walk through the door as we sat with Mom, but it soon dawned on us that he wouldn’t be coming either. Instead, the phone rang. Another convention upended by COVID-19: telephonic last rites were given. If I could manage hypertension over the phone, as I had been doing for 6 weeks, why couldn’t we pray on a conference call? It worked: the timeless words of reassurance given, with my sister administering divine unction on our mother’s forehead on the priest’s behalf.
A sense of peace descended in the room when he finished. The vasopressors were stopped, and we turned off the lights, growing quiet while we waited. By this time, Mom had tested negative for COVID-19 twice. I got in bed with her that night and held her for the first time in weeks. I knew she wouldn’t infect me. Since she was dying, I didn’t care about my risk to her.
But Mom didn’t die. She slept soundly. Despite comfort care orders, the next morning her vital signs were taken, showing remarkable improvement. Although not normal, she had stabilized overnight. What was initially thought to be sepsis or another myocardial infarction likely was a vagal episode superimposed on some hypovolemia. After more discussions, we decided to restart the noncritical care she had been receiving the day before and suspend comfort-only measures.
How grateful we were that she lived and that she was improving. But the cruel COVID-19 irony declared itself again. Now that she was getting better, we were once again banished from her side. She was alone again, fighting hard, but alive.
Mom is back home, gaining strength every day—battling her chronic illnesses, but like all of us, still menaced by COVID-19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We made the call to bring her in for a serious but treatable illness while risking infection with COVID-19 but questioned whether we should have until she was placed in the ambulance. Of the cruelties associated with the pandemic, and there are many, the most ironic was that the only way I could be close to Mom was when we almost lost her. We are starved for physical contact with our loved ones, many of the most vulnerable, who must distance like their lives depend upon it. Because of course they just might.
Section Editor: Preeti Malani, MD, MSJ, Associate Editor.
Corresponding Author: Katherine C. McKenzie, MD, Yale Center for Asylum Medicine,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367 Cedar St, Yale School of Medicine, New Haven, CT 06510 (katherine.mckenzie@yale.edu).
Published Online: June 30, 2020. doi:10.1001/jama.2020.11882
Conflict of Interest Disclosures: None reported.
Additional Contributions: I thank my mother for allowing me to share this story.
芝加哥的COVID-19病毒株与武汉类似
COVID-19大流行的趋势:从过去看未来
(一)前言
根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中国学者学术论文报道,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冠状病毒-2(SARS-CoV-2)(引起COVID-19的病毒, 网络又称新冠病毒)于2019年12月8日在中国武汉首例出现。那时即使是最有经验的国际公共卫生专家都不能预料它将会迅速地在全球蔓延,会造成这样一个100多年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笔者当时认为病毒可能会传播至他国如美国,但沒预见到当今如此严重的全球性大流行。
2020年1月,一些公共卫生官员开始拉响警报,但直到2020年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才宣布Covid-19全球大流行。
Covid-19的病毒着实把全球各国弄得措手不及,而且人们对其未来发展情况仍然是高度地不可预测,也没有清楚的知识去指导如何去最终地控制这个大流行。
其他两种动物传人的冠状病毒病如SARS(莎士,非典,即由SARS-CoV-1病毒引起的一种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和中东呼吸综合征的冠状病毒[MERS-CoV]的流行病学与SARS-CoV-2有很大的不同;因此,这两种病原体无法为Covid-19提供有用的模型来预测新冠这种大流行预期的结果。
专家认为(The CIDRAP 报告)最好的用来比较的模型是大流行流感。自1700年代初期以来,全球至少已经发生过八次流感大流行,其中四起发生于20世纪(1918-1919、1957、1968)和本世纪2009-2010。当我们试图预测未来情景时,我们可以也必须从过去的流感大流行中学习从而认识当今的COVID-19大流行。通过将COVID-19和流感大流行进行比较,可以帮助我们来预想当前COVID-19大流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N种情况。
目前很多模式主要聚焦在北半球,但是类似的模式也可能发生在南半球。由于南半球缺乏健全的医疗基础设施(包括缺乏足够的医疗设施,个人防护装备)和合并其他疾病,例如其他感染(例如HIV,TB,疟疾),营养不良,南半球某些地区的慢性呼吸道疾病甚至可能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大流行。
(二)Covid-19 和流感大流行的流行病学异同
两者的相似处:
即使冠状病毒与流感病毒从许多方面来说都大不相同,然而COVID-19大流行和流感大流行也有几个重要的相似之处。
首先,SARS-CoV-2和大流行性流感病毒均是新型病毒病原体,全球人口在流行时对这些病毒几乎没有免疫力,从而导致全球人类对病毒的极度敏感性。
其次,SARS-CoV-2和流感病毒均主要通过呼吸道大液滴传播,而且两者均还有较小部分通过气溶胶传播。
第三,两种病毒也都存在无症状传播,从而促进了传播。
最后,两种病毒均能够感染数以百万计的人,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地流行传播。
两者的重要区别:
首先,是潜伏期的不同; 流感的平均潜伏期为2天(范围为1至4天);而COVID-19的平均潜伏期为5天(范围,2至14天)。COVID-19的潜伏期较长,使得病毒可以在被发现之前已经在的不同人群中悄悄地传播。这促成了各国政府在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之前的那种不屑一顾的自满情绪。
其次,这个重要不同因素是无症状感染部分。虽然确切信息仍然在收集中,公共卫生官员表示 25%的COVID-19病例可能是无症状的,不久更好的血清学研究可能会将此百分比向上调高。许多研究已经探索了无症状的流感。一个综述文献发现了一个无症状流感传播者的平均值为16%(范围为4%至28%)。因此,尽管两种病毒都可以导致无症状感染,但COVID-19的无症状分数似乎比流感要高。
第三,这个考虑因素是病人症状发生前病毒传播的时间框架。最近一研究发现,SARS-CoV-2病毒载量在症状发作时最高,表明病毒传播,可能在症状发生之前达到峰值,导致大量的症状前传播。对疗养院居民中SARS-CoV-2的点普遍性研究表明,27名居民测试时无症状,中位4天后24名出现症状(3至5天),支持症状前病毒传播的可能性。对于H1N1大流行性甲型流感病毒,一项研究表明,病毒性传播在症状出现后的第一到第二天达到峰值,也支持流感大流行的病毒症状前传染性不及SARS-Cov-2。
以上所有因素均有助于病毒的传播。
|
|
量化病毒传播能力的一种方法是确定该病毒的基本繁殖数(Basic reproductive number, R0)。R0是单个感染者在完全易感人群中导致新感染人数的平均数量。
R0可能会因以下因素而改变:
影响人与人之间的接触率,例如身体疏远策略和禁足居家令,旨在将R0降低到小于1。当R0低于1时,表明传染爆发是在缩小而不是扩大,因为每个感染者随后感染了少于1个他人。
虽然R0不受群体免疫力的影响(即对病毒免疫的人口比例,这种群体免疫或由自然感染或疫苗接种免疫产生),但是在人口中免疫力可以影响有效繁殖数(effective reproductive number, RE),RE与R0类似,只是RE不依赖于拥有完全易感人群的信息。
人群中的免疫力可以通过将RE降低到1以下而有效地减少或消除传染的爆发。
SARS-CoV-2 中国流行初期的R0估计为2.0至2.5。但是,各个地理区域 的SARS-CoV-2的R0很难得到准确确定,因为识别和测试感染者的能力很受挑战,一项研究表明,其数值可能会是更高,有人认为达到了5。另外,对于SARS-CoV-2,每个人的R0都不相同;它可以因受感染者病毒传播的自然变异性而改变。甚至R0的平均值也不是纯生物量-它取决于行为和接触方式。例如,有人推测在人口稠密或接触频繁的地区(例如大城市),SARS-CoV-2的R0可能更高。
此外,一些证据表明某些人是“超级传播者”,就像在MERS-CoV和
SARS。一些国家通过缓解措施似乎已经能够为将SARS-CoV-2的R0降到低于1,然而随着缓解措施的取消,任何给定区域中的R0可能又会爬回1以上,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导致疾病复发。
大流行性流感的R0因大流行而异,但估计一直在2左右或以下,这表明即使是过去的严重流感大流行病毒也比SARS-CoV-2的传播性小。
一个在2009-10年大流行之后发表的评论文章对报告R0值的最新研究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四个流感大流行。尽管结果有所不同,但最高的中位数R0与1918年和1968年的流感大流行(均为1.8),其次是1957年的大流行(1.65),然后是2009-10年的大流行(1.46)。相比之下,季节性流感大流行的中位数R0为1.27。
(三)以往流感大流行的主要教训
自1700年代初以来发生的八次主要流行病中,大多数流行没有明显的季节性模式。
各个地理区域中,北半球的冬季有两次,春季的三次,夏季的一次,秋季的两次。
七次有早期高峰,然后在几个月内就消失了,没有大量的人群涉及。随后,这七个峰中的每一个在第一次峰后约6个月都有第二次实质性高峰出现。在最初的流行之后的两年内,一些流行病显示出较小的流行病例。
唯一的1968年的大流行开始于更传统的流感样季节性流行,在北半球出现了一个深秋/冬季波,第二个冬天又是第二波。在某些地区,特别是在欧洲,与大流行相关的死亡率第二年更高。
除了2009-2010年那次大流行外,这些大流行的过程并未受到疫苗接种运动的实质性影响,在此期间大约在大流行的开始6个月后美国才开始使用疫苗,直到大流行之后在美国大部分地区达到顶峰时,才可获得大量疫苗。
一份报告估计,在美国,通过疫苗接种计划,预防了70万到1百50万临床病例,4千到1万例住院和200到500例死亡。
自1900年以来发生了三场大流行之后,甲型流感大流行逐渐变得更适合人类,并取代了主要的季节性传播的流感病毒,成了每年鉴定出主要的季节性甲型流感毒株。在2009-2010年大流行之后,大流行性流感H1N1菌株与甲型H3N2流感在季节性上两者共同传播。
观察过去流感大流行的流行病学的关键点,可借鉴并预测COVID-19大流行可能会有以下可能性:
首先,大流行的持续时间可能为18到24个月,因为群体免疫需时间逐渐达到。据有限的血清监测,表明群体将需要时间,迄今可获得的数据表明,人群中只有一小部分受到感染,且感染率因地区而异。鉴于SARS-CoV-2的可传播性,需要60%-70%人群获取免疫以达到群体免疫的关键阈值才能阻止大流行。
由于我们尚不知道对天然SARS-CoV-2的免疫力持续时间,这可能会使情况变得复杂(可能短至几个月或长达几年)。根据季节性冠状病毒,我们可以预见,即使暴露后免疫力随时间下降,仍然可能会有一定降低疾病严重程度和降低传染性这种保护作用,当然这对于SARS-CoV-2仍有待评估。
大流行过程也可能受到疫苗的影响;但是,直到至少要等到2021年的某个时候,最快也要今年底。我们不知道在疫苗开发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这可能会延迟时间表。
其次,COVID-19大流行的未来存在几种不同的情况,其中一些是与过去的流感大流行期间发生的情况一致。这些可以总结如下,分别是三种可能的情景,如下图所示(横轴是时间, 纵轴是病例数):
情景1:2020年春季的COVID-19是第一波,随后是一系列发生在整个夏季重复的较小波,然后持续1-2年,并在2021年消失。这些波的发生与地区,缓解措施,以及如何解除缓解的方法有关。如果是这种情景,那么在接下来的1至2年里,根据波峰的高度,这种情况可能需要定期恢复缓解措施,并且随后放宽这些缓解措接。
情景2:2020年春季第一波COVID-19,之后是秋天或冬天的大波,和随后的一个或多个较小波,这种模式需要在2021年秋季时恢复采取缓解措施,以期降低感染传播,预防医疗保健系统挤兑。这种模式与1918-19年大流行相似。在那次大流行中,开始于1918年3月时有一小波,小波于夏季消停了几个月。然后在1918年秋天,冬季,1919年春天出现一个更大的峰值。1919年的那个波,标志着大流行病的终结。
1957-58年大流行遵循类似的模式,但规模较小,始于春季浪潮,随后是更大的秋季浪潮,连续的小波浪,持续发生了数年。
2009-10年大流行也遵循了始于春季的模式,在春季波之后是更大的下降波。
情景3:2020年春季的第一波COVID-19浪潮之后,持续的“缓慢燃烧”地传播和不停有新病例的发生,但没有清晰的波形。同样,此模式可能会有所不同,在地理上可能会受到各个地区所采取的缓解措施程度的影响。
而在过去的流感大流行中没有发现这第三种模式,它仍然有可能发生在COVID-19流行上。这第三种情况可能不需要恢复缓解措施,尽管案例和死亡仍将继续发生。
无论大流行发生在哪种情况下(假设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持续实施缓解措施),我们必须为至少18至24个月的重要COVID-19活动做好准备,并出现热点定期在不同的地理区域内。随着大流行的减弱,SARS-CoV-2很可能会继续会在人群中传播,并将与季节性模式同步,严重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与其他病原性较低的冠状病毒一样,例如β冠状病毒OC43和HKU1(Kissler 2020)和过去的大流行性流感病毒都是这样的。
在年初,笔者曾认为covid-19与莎士一样,会在夏天来临的时候消失,看来这对covid-19影响是低估了,这种在夏天突然消失不再重来的可能性较小,我们必须准备更可能的1-2年疫情反反复复。大家不要为谁对谁错甩来甩去,这影响了全球近两百个国家地区的大流行,怎么可能是哪一人哪一国的失误呢?反过来说,人们又为什么不从中找出问题的关键所在以避免再次发生呢?
|
|
芝加哥的COVID-19病毒株与武汉类似
COVID-19大流行的趋势:从过去看未来
(一)前言
根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中国学者学术论文报道,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冠状病毒-2(SARS-CoV-2)(引起COVID-19的病毒, 网络又称新冠病毒)于2019年12月8日在中国武汉首例出现。那时即使是最有经验的国际公共卫生专家都不能预料它将会迅速地在全球蔓延,会造成这样一个100多年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笔者当时认为病毒可能会传播至他国如美国,但沒预见到当今如此严重的全球性大流行。
2020年1月,一些公共卫生官员开始拉响警报,但直到2020年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才宣布Covid-19全球大流行。
Covid-19的病毒着实把全球各国弄得措手不及,而且人们对其未来发展情况仍然是高度地不可预测,也没有清楚的知识去指导如何去最终地控制这个大流行。
其他两种动物传人的冠状病毒病如SARS(莎士,非典,即由SARS-CoV-1病毒引起的一种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和中东呼吸综合征的冠状病毒[MERS-CoV]的流行病学与SARS-CoV-2有很大的不同;因此,这两种病原体无法为Covid-19提供有用的模型来预测新冠这种大流行预期的结果。
专家认为(The CIDRAP 报告)最好的用来比较的模型是大流行流感。自1700年代初期以来,全球至少已经发生过八次流感大流行,其中四起发生于20世纪(1918-1919、1957、1968)和本世纪2009-2010。当我们试图预测未来情景时,我们可以也必须从过去的流感大流行中学习从而认识当今的COVID-19大流行。通过将COVID-19和流感大流行进行比较,可以帮助我们来预想当前COVID-19大流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N种情况。
目前很多模式主要聚焦在北半球,但是类似的模式也可能发生在南半球。由于南半球缺乏健全的医疗基础设施(包括缺乏足够的医疗设施,个人防护装备)和合并其他疾病,例如其他感染(例如HIV,TB,疟疾),营养不良,南半球某些地区的慢性呼吸道疾病甚至可能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大流行。
(二)Covid-19 和流感大流行的流行病学异同
两者的相似处:
即使冠状病毒与流感病毒从许多方面来说都大不相同,然而COVID-19大流行和流感大流行也有几个重要的相似之处。
首先,SARS-CoV-2和大流行性流感病毒均是新型病毒病原体,全球人口在流行时对这些病毒几乎没有免疫力,从而导致全球人类对病毒的极度敏感性。
其次,SARS-CoV-2和流感病毒均主要通过呼吸道大液滴传播,而且两者均还有较小部分通过气溶胶传播。
第三,两种病毒也都存在无症状传播,从而促进了传播。
最后,两种病毒均能够感染数以百万计的人,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地流行传播。
两者的重要区别:
首先,是潜伏期的不同; 流感的平均潜伏期为2天(范围为1至4天);而COVID-19的平均潜伏期为5天(范围,2至14天)。COVID-19的潜伏期较长,使得病毒可以在被发现之前已经在的不同人群中悄悄地传播。这促成了各国政府在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之前的那种不屑一顾的自满情绪。
其次,这个重要不同因素是无症状感染部分。虽然确切信息仍然在收集中,公共卫生官员表示 25%的COVID-19病例可能是无症状的,不久更好的血清学研究可能会将此百分比向上调高。许多研究已经探索了无症状的流感。一个综述文献发现了一个无症状流感传播者的平均值为16%(范围为4%至28%)。因此,尽管两种病毒都可以导致无症状感染,但COVID-19的无症状分数似乎比流感要高。
第三,这个考虑因素是病人症状发生前病毒传播的时间框架。最近一研究发现,SARS-CoV-2病毒载量在症状发作时最高,表明病毒传播,可能在症状发生之前达到峰值,导致大量的症状前传播。对疗养院居民中SARS-CoV-2的点普遍性研究表明,27名居民测试时无症状,中位4天后24名出现症状(3至5天),支持症状前病毒传播的可能性。对于H1N1大流行性甲型流感病毒,一项研究表明,病毒性传播在症状出现后的第一到第二天达到峰值,也支持流感大流行的病毒症状前传染性不及SARS-Cov-2。
以上所有因素均有助于病毒的传播。
|
|
量化病毒传播能力的一种方法是确定该病毒的基本繁殖数(Basic reproductive number, R0)。R0是单个感染者在完全易感人群中导致新感染人数的平均数量。
R0可能会因以下因素而改变:
影响人与人之间的接触率,例如身体疏远策略和禁足居家令,旨在将R0降低到小于1。当R0低于1时,表明传染爆发是在缩小而不是扩大,因为每个感染者随后感染了少于1个他人。
虽然R0不受群体免疫力的影响(即对病毒免疫的人口比例,这种群体免疫或由自然感染或疫苗接种免疫产生),但是在人口中免疫力可以影响有效繁殖数(effective reproductive number, RE),RE与R0类似,只是RE不依赖于拥有完全易感人群的信息。
人群中的免疫力可以通过将RE降低到1以下而有效地减少或消除传染的爆发。
SARS-CoV-2 中国流行初期的R0估计为2.0至2.5。但是,各个地理区域 的SARS-CoV-2的R0很难得到准确确定,因为识别和测试感染者的能力很受挑战,一项研究表明,其数值可能会是更高,有人认为达到了5。另外,对于SARS-CoV-2,每个人的R0都不相同;它可以因受感染者病毒传播的自然变异性而改变。甚至R0的平均值也不是纯生物量-它取决于行为和接触方式。例如,有人推测在人口稠密或接触频繁的地区(例如大城市),SARS-CoV-2的R0可能更高。
此外,一些证据表明某些人是“超级传播者”,就像在MERS-CoV和
SARS。一些国家通过缓解措施似乎已经能够为将SARS-CoV-2的R0降到低于1,然而随着缓解措施的取消,任何给定区域中的R0可能又会爬回1以上,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导致疾病复发。
大流行性流感的R0因大流行而异,但估计一直在2左右或以下,这表明即使是过去的严重流感大流行病毒也比SARS-CoV-2的传播性小。
一个在2009-10年大流行之后发表的评论文章对报告R0值的最新研究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四个流感大流行。尽管结果有所不同,但最高的中位数R0与1918年和1968年的流感大流行(均为1.8),其次是1957年的大流行(1.65),然后是2009-10年的大流行(1.46)。相比之下,季节性流感大流行的中位数R0为1.27。
(三)以往流感大流行的主要教训
自1700年代初以来发生的八次主要流行病中,大多数流行没有明显的季节性模式。
各个地理区域中,北半球的冬季有两次,春季的三次,夏季的一次,秋季的两次。
七次有早期高峰,然后在几个月内就消失了,没有大量的人群涉及。随后,这七个峰中的每一个在第一次峰后约6个月都有第二次实质性高峰出现。在最初的流行之后的两年内,一些流行病显示出较小的流行病例。
唯一的1968年的大流行开始于更传统的流感样季节性流行,在北半球出现了一个深秋/冬季波,第二个冬天又是第二波。在某些地区,特别是在欧洲,与大流行相关的死亡率第二年更高。
除了2009-2010年那次大流行外,这些大流行的过程并未受到疫苗接种运动的实质性影响,在此期间大约在大流行的开始6个月后美国才开始使用疫苗,直到大流行之后在美国大部分地区达到顶峰时,才可获得大量疫苗。
一份报告估计,在美国,通过疫苗接种计划,预防了70万到1百50万临床病例,4千到1万例住院和200到500例死亡。
自1900年以来发生了三场大流行之后,甲型流感大流行逐渐变得更适合人类,并取代了主要的季节性传播的流感病毒,成了每年鉴定出主要的季节性甲型流感毒株。在2009-2010年大流行之后,大流行性流感H1N1菌株与甲型H3N2流感在季节性上两者共同传播。
观察过去流感大流行的流行病学的关键点,可借鉴并预测COVID-19大流行可能会有以下可能性:
首先,大流行的持续时间可能为18到24个月,因为群体免疫需时间逐渐达到。据有限的血清监测,表明群体将需要时间,迄今可获得的数据表明,人群中只有一小部分受到感染,且感染率因地区而异。鉴于SARS-CoV-2的可传播性,需要60%-70%人群获取免疫以达到群体免疫的关键阈值才能阻止大流行。
由于我们尚不知道对天然SARS-CoV-2的免疫力持续时间,这可能会使情况变得复杂(可能短至几个月或长达几年)。根据季节性冠状病毒,我们可以预见,即使暴露后免疫力随时间下降,仍然可能会有一定降低疾病严重程度和降低传染性这种保护作用,当然这对于SARS-CoV-2仍有待评估。
大流行过程也可能受到疫苗的影响;但是,直到至少要等到2021年的某个时候,最快也要今年底。我们不知道在疫苗开发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这可能会延迟时间表。
其次,COVID-19大流行的未来存在几种不同的情况,其中一些是与过去的流感大流行期间发生的情况一致。这些可以总结如下,分别是三种可能的情景,如下图所示(横轴是时间, 纵轴是病例数):
情景1:2020年春季的COVID-19是第一波,随后是一系列发生在整个夏季重复的较小波,然后持续1-2年,并在2021年消失。这些波的发生与地区,缓解措施,以及如何解除缓解的方法有关。如果是这种情景,那么在接下来的1至2年里,根据波峰的高度,这种情况可能需要定期恢复缓解措施,并且随后放宽这些缓解措接。
情景2:2020年春季第一波COVID-19,之后是秋天或冬天的大波,和随后的一个或多个较小波,这种模式需要在2021年秋季时恢复采取缓解措施,以期降低感染传播,预防医疗保健系统挤兑。这种模式与1918-19年大流行相似。在那次大流行中,开始于1918年3月时有一小波,小波于夏季消停了几个月。然后在1918年秋天,冬季,1919年春天出现一个更大的峰值。1919年的那个波,标志着大流行病的终结。
1957-58年大流行遵循类似的模式,但规模较小,始于春季浪潮,随后是更大的秋季浪潮,连续的小波浪,持续发生了数年。
2009-10年大流行也遵循了始于春季的模式,在春季波之后是更大的下降波。
情景3:2020年春季的第一波COVID-19浪潮之后,持续的“缓慢燃烧”地传播和不停有新病例的发生,但没有清晰的波形。同样,此模式可能会有所不同,在地理上可能会受到各个地区所采取的缓解措施程度的影响。
而在过去的流感大流行中没有发现这第三种模式,它仍然有可能发生在COVID-19流行上。这第三种情况可能不需要恢复缓解措施,尽管案例和死亡仍将继续发生。
无论大流行发生在哪种情况下(假设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持续实施缓解措施),我们必须为至少18至24个月的重要COVID-19活动做好准备,并出现热点定期在不同的地理区域内。随着大流行的减弱,SARS-CoV-2很可能会继续会在人群中传播,并将与季节性模式同步,严重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与其他病原性较低的冠状病毒一样,例如β冠状病毒OC43和HKU1(Kissler 2020)和过去的大流行性流感病毒都是这样的。
在年初,笔者曾认为covid-19与莎士一样,会在夏天来临的时候消失,看来这对covid-19影响是低估了,这种在夏天突然消失不再重来的可能性较小,我们必须准备更可能的1-2年疫情反反复复。大家不要为谁对谁错甩来甩去,这影响了全球近两百个国家地区的大流行,怎么可能是哪一人哪一国的失误呢?反过来说,人们又为什么不从中找出问题的关键所在以避免再次发生呢?
|
|
芝加哥的COVID-19病毒株与武汉类似
COVID-19大流行的趋势:从过去看未来
(一)前言
根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中国学者学术论文报道,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冠状病毒-2(SARS-CoV-2)(引起COVID-19的病毒, 网络又称新冠病毒)于2019年12月8日在中国武汉首例出现。那时即使是最有经验的国际公共卫生专家都不能预料它将会迅速地在全球蔓延,会造成这样一个100多年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笔者当时认为病毒可能会传播至他国如美国,但沒预见到当今如此严重的全球性大流行。
2020年1月,一些公共卫生官员开始拉响警报,但直到2020年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才宣布Covid-19全球大流行。
Covid-19的病毒着实把全球各国弄得措手不及,而且人们对其未来发展情况仍然是高度地不可预测,也没有清楚的知识去指导如何去最终地控制这个大流行。
其他两种动物传人的冠状病毒病如SARS(莎士,非典,即由SARS-CoV-1病毒引起的一种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和中东呼吸综合征的冠状病毒[MERS-CoV]的流行病学与SARS-CoV-2有很大的不同;因此,这两种病原体无法为Covid-19提供有用的模型来预测新冠这种大流行预期的结果。
专家认为(The CIDRAP 报告)最好的用来比较的模型是大流行流感。自1700年代初期以来,全球至少已经发生过八次流感大流行,其中四起发生于20世纪(1918-1919、1957、1968)和本世纪2009-2010。当我们试图预测未来情景时,我们可以也必须从过去的流感大流行中学习从而认识当今的COVID-19大流行。通过将COVID-19和流感大流行进行比较,可以帮助我们来预想当前COVID-19大流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N种情况。
目前很多模式主要聚焦在北半球,但是类似的模式也可能发生在南半球。由于南半球缺乏健全的医疗基础设施(包括缺乏足够的医疗设施,个人防护装备)和合并其他疾病,例如其他感染(例如HIV,TB,疟疾),营养不良,南半球某些地区的慢性呼吸道疾病甚至可能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大流行。
(二)Covid-19 和流感大流行的流行病学异同
两者的相似处:
即使冠状病毒与流感病毒从许多方面来说都大不相同,然而COVID-19大流行和流感大流行也有几个重要的相似之处。
首先,SARS-CoV-2和大流行性流感病毒均是新型病毒病原体,全球人口在流行时对这些病毒几乎没有免疫力,从而导致全球人类对病毒的极度敏感性。
其次,SARS-CoV-2和流感病毒均主要通过呼吸道大液滴传播,而且两者均还有较小部分通过气溶胶传播。
第三,两种病毒也都存在无症状传播,从而促进了传播。
最后,两种病毒均能够感染数以百万计的人,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地流行传播。
两者的重要区别:
首先,是潜伏期的不同; 流感的平均潜伏期为2天(范围为1至4天);而COVID-19的平均潜伏期为5天(范围,2至14天)。COVID-19的潜伏期较长,使得病毒可以在被发现之前已经在的不同人群中悄悄地传播。这促成了各国政府在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之前的那种不屑一顾的自满情绪。
其次,这个重要不同因素是无症状感染部分。虽然确切信息仍然在收集中,公共卫生官员表示 25%的COVID-19病例可能是无症状的,不久更好的血清学研究可能会将此百分比向上调高。许多研究已经探索了无症状的流感。一个综述文献发现了一个无症状流感传播者的平均值为16%(范围为4%至28%)。因此,尽管两种病毒都可以导致无症状感染,但COVID-19的无症状分数似乎比流感要高。
第三,这个考虑因素是病人症状发生前病毒传播的时间框架。最近一研究发现,SARS-CoV-2病毒载量在症状发作时最高,表明病毒传播,可能在症状发生之前达到峰值,导致大量的症状前传播。对疗养院居民中SARS-CoV-2的点普遍性研究表明,27名居民测试时无症状,中位4天后24名出现症状(3至5天),支持症状前病毒传播的可能性。对于H1N1大流行性甲型流感病毒,一项研究表明,病毒性传播在症状出现后的第一到第二天达到峰值,也支持流感大流行的病毒症状前传染性不及SARS-Cov-2。
以上所有因素均有助于病毒的传播。
|
|
量化病毒传播能力的一种方法是确定该病毒的基本繁殖数(Basic reproductive number, R0)。R0是单个感染者在完全易感人群中导致新感染人数的平均数量。
R0可能会因以下因素而改变:
影响人与人之间的接触率,例如身体疏远策略和禁足居家令,旨在将R0降低到小于1。当R0低于1时,表明传染爆发是在缩小而不是扩大,因为每个感染者随后感染了少于1个他人。
虽然R0不受群体免疫力的影响(即对病毒免疫的人口比例,这种群体免疫或由自然感染或疫苗接种免疫产生),但是在人口中免疫力可以影响有效繁殖数(effective reproductive number, RE),RE与R0类似,只是RE不依赖于拥有完全易感人群的信息。
人群中的免疫力可以通过将RE降低到1以下而有效地减少或消除传染的爆发。
SARS-CoV-2 中国流行初期的R0估计为2.0至2.5。但是,各个地理区域 的SARS-CoV-2的R0很难得到准确确定,因为识别和测试感染者的能力很受挑战,一项研究表明,其数值可能会是更高,有人认为达到了5。另外,对于SARS-CoV-2,每个人的R0都不相同;它可以因受感染者病毒传播的自然变异性而改变。甚至R0的平均值也不是纯生物量-它取决于行为和接触方式。例如,有人推测在人口稠密或接触频繁的地区(例如大城市),SARS-CoV-2的R0可能更高。
此外,一些证据表明某些人是“超级传播者”,就像在MERS-CoV和
SARS。一些国家通过缓解措施似乎已经能够为将SARS-CoV-2的R0降到低于1,然而随着缓解措施的取消,任何给定区域中的R0可能又会爬回1以上,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导致疾病复发。
大流行性流感的R0因大流行而异,但估计一直在2左右或以下,这表明即使是过去的严重流感大流行病毒也比SARS-CoV-2的传播性小。
一个在2009-10年大流行之后发表的评论文章对报告R0值的最新研究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四个流感大流行。尽管结果有所不同,但最高的中位数R0与1918年和1968年的流感大流行(均为1.8),其次是1957年的大流行(1.65),然后是2009-10年的大流行(1.46)。相比之下,季节性流感大流行的中位数R0为1.27。
(三)以往流感大流行的主要教训
自1700年代初以来发生的八次主要流行病中,大多数流行没有明显的季节性模式。
各个地理区域中,北半球的冬季有两次,春季的三次,夏季的一次,秋季的两次。
七次有早期高峰,然后在几个月内就消失了,没有大量的人群涉及。随后,这七个峰中的每一个在第一次峰后约6个月都有第二次实质性高峰出现。在最初的流行之后的两年内,一些流行病显示出较小的流行病例。
唯一的1968年的大流行开始于更传统的流感样季节性流行,在北半球出现了一个深秋/冬季波,第二个冬天又是第二波。在某些地区,特别是在欧洲,与大流行相关的死亡率第二年更高。
除了2009-2010年那次大流行外,这些大流行的过程并未受到疫苗接种运动的实质性影响,在此期间大约在大流行的开始6个月后美国才开始使用疫苗,直到大流行之后在美国大部分地区达到顶峰时,才可获得大量疫苗。
一份报告估计,在美国,通过疫苗接种计划,预防了70万到1百50万临床病例,4千到1万例住院和200到500例死亡。
自1900年以来发生了三场大流行之后,甲型流感大流行逐渐变得更适合人类,并取代了主要的季节性传播的流感病毒,成了每年鉴定出主要的季节性甲型流感毒株。在2009-2010年大流行之后,大流行性流感H1N1菌株与甲型H3N2流感在季节性上两者共同传播。
观察过去流感大流行的流行病学的关键点,可借鉴并预测COVID-19大流行可能会有以下可能性:
首先,大流行的持续时间可能为18到24个月,因为群体免疫需时间逐渐达到。据有限的血清监测,表明群体将需要时间,迄今可获得的数据表明,人群中只有一小部分受到感染,且感染率因地区而异。鉴于SARS-CoV-2的可传播性,需要60%-70%人群获取免疫以达到群体免疫的关键阈值才能阻止大流行。
由于我们尚不知道对天然SARS-CoV-2的免疫力持续时间,这可能会使情况变得复杂(可能短至几个月或长达几年)。根据季节性冠状病毒,我们可以预见,即使暴露后免疫力随时间下降,仍然可能会有一定降低疾病严重程度和降低传染性这种保护作用,当然这对于SARS-CoV-2仍有待评估。
大流行过程也可能受到疫苗的影响;但是,直到至少要等到2021年的某个时候,最快也要今年底。我们不知道在疫苗开发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这可能会延迟时间表。
其次,COVID-19大流行的未来存在几种不同的情况,其中一些是与过去的流感大流行期间发生的情况一致。这些可以总结如下,分别是三种可能的情景,如下图所示(横轴是时间, 纵轴是病例数):
情景1:2020年春季的COVID-19是第一波,随后是一系列发生在整个夏季重复的较小波,然后持续1-2年,并在2021年消失。这些波的发生与地区,缓解措施,以及如何解除缓解的方法有关。如果是这种情景,那么在接下来的1至2年里,根据波峰的高度,这种情况可能需要定期恢复缓解措施,并且随后放宽这些缓解措接。
情景2:2020年春季第一波COVID-19,之后是秋天或冬天的大波,和随后的一个或多个较小波,这种模式需要在2021年秋季时恢复采取缓解措施,以期降低感染传播,预防医疗保健系统挤兑。这种模式与1918-19年大流行相似。在那次大流行中,开始于1918年3月时有一小波,小波于夏季消停了几个月。然后在1918年秋天,冬季,1919年春天出现一个更大的峰值。1919年的那个波,标志着大流行病的终结。
1957-58年大流行遵循类似的模式,但规模较小,始于春季浪潮,随后是更大的秋季浪潮,连续的小波浪,持续发生了数年。
2009-10年大流行也遵循了始于春季的模式,在春季波之后是更大的下降波。
情景3:2020年春季的第一波COVID-19浪潮之后,持续的“缓慢燃烧”地传播和不停有新病例的发生,但没有清晰的波形。同样,此模式可能会有所不同,在地理上可能会受到各个地区所采取的缓解措施程度的影响。
而在过去的流感大流行中没有发现这第三种模式,它仍然有可能发生在COVID-19流行上。这第三种情况可能不需要恢复缓解措施,尽管案例和死亡仍将继续发生。
无论大流行发生在哪种情况下(假设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持续实施缓解措施),我们必须为至少18至24个月的重要COVID-19活动做好准备,并出现热点定期在不同的地理区域内。随着大流行的减弱,SARS-CoV-2很可能会继续会在人群中传播,并将与季节性模式同步,严重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与其他病原性较低的冠状病毒一样,例如β冠状病毒OC43和HKU1(Kissler 2020)和过去的大流行性流感病毒都是这样的。
在年初,笔者曾认为covid-19与莎士一样,会在夏天来临的时候消失,看来这对covid-19影响是低估了,这种在夏天突然消失不再重来的可能性较小,我们必须准备更可能的1-2年疫情反反复复。大家不要为谁对谁错甩来甩去,这影响了全球近两百个国家地区的大流行,怎么可能是哪一人哪一国的失误呢?反过来说,人们又为什么不从中找出问题的关键所在以避免再次发生呢?
|
|
ANACP COVID19北美系列讲座:相关心理问题及干预
ANACP COVID19北美系列讲座:
相关心理问题及干预
4/26/2020
整理记录者 董蓓莉
北美华人医师联盟邀请到三位精神科医生为大家分享
伍波医生UT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 at Dallas 精神科急诊
COVID 19下的心理干预
人类对灾难性创伤的反应非常复杂。在COVID 19大流行中,截止2020年4月26日上午,已经有205,142人死亡,2,934,141确诊病例,超过200个国家的人受到影响, 经济损失超过上亿美元。
在不同类型的灾难中,自然灾害引起的精神健康后果通常相对比较轻。涉及人为错误而非故意的技术事故可能会产生更大的精神病理改变。故意的人为事件或者恐怖行为则可能造成最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
然而所有灾难都可能引发各种急性痛苦,甚至导致长期困扰。短期问题包括焦虑,恐惧,失眠,抑郁,绝望,愤怒,悲伤,吸毒,家庭不和,虐待儿童,家庭暴力甚至自杀的念头。长期或慢性问题则有重度抑郁症,创伤后综合征(PTSD),物质(substance)使用障碍,等等。
COVID 19大流行与自然灾害不同。地震,火山,飓风或海啸往往是突然发生,发生时间短暂,以分,小时或天数计算。而COVID 19的发生时间则是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以天,周,月来衡量,因而更容易造成倦怠。而其长期影响更是难以估计的巨大。
医护专业人员在COVID19 大流行中,有多重角色:
也是这种大流行的受害者,也可能患COVID 19
是治疗和帮助COVID 19患者及其家人的专业人士
感染COVID 19或被暴露的风险要高得多;甚至我们的家庭也面临着更高的风险
是家庭成员,朋友,社区的资源,提供建议和技巧,尽管我们也正在从他人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学习COVID 19及其影响
过度操劳
有时会缺乏防护。
可能会受到侮辱,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受到歧视
我们被称为“英雄”,但我们有自己的焦虑和恐惧:担心我们自己,家人和病人的安全。
这种恐惧每天都在我们去医院或诊所时重复。
我们应该如何回应?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我们应该如何保护自己并最大限度地帮助我们的患者和社区呢?
中国武汉的医护人员所经历的情绪阶段:困惑,震惊,愤怒,焦虑,倦怠,绝望,接受,希望,康复,后果。
这几个阶段可能有重叠,或顺序有交替。而在海外的华人医务工作者,因为基本上都不同程度的参与了在中国的”上半场“抗役,到现在全球的”下半场“抗役,更可能经历倦怠。
作为应急反应,“逃跑或战斗”(Fight or flight response) 帮助我们离开或者积极面对危险来保护自己。而保持积极的自我概念和充满希望,可以帮助个人寻求支持,并增强与其他支持者结盟的能力,以增强应对危机的韧性(resilience)。
COVID 19可以发生在任何人群。“社交隔离”,或者准确地一点地说“人与人的物理距离”,是阻止传染的有效办法。然而,对于医务工作者来说,逃离是不可行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一直与患者直接接触。现代科技让我们能够进行远程医疗。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焦虑和直接暴露于COVID19。
为了更好地抗疫
1. 不停地学习知识-仅ANACP,迄今已举办了18个在线研讨会,其中包括临床医生和科学家。
需要遵循指南,阅读期刊出版物,参加有公信力的研讨会,听取有公信力的媒体报道以及与可信赖同事的讨论。
但不要陷入知识爆炸之中,不要同时成为病毒学家,流行病学家,临床医生,重症监护专家,药理学家,精神病学家,科学家,物流专家;不要被海量的真假信息搞得焦虑和无所适从。
2. 要做好准备-从个人防护用品到看护孩子。敢于询问,要求,要有说服力和创造力,等。
3. 具有自我控制
专注于工作,要有休息,哪怕很短暂
自我补充
通过放松:淋浴,良好睡眠,均衡饮食,唱歌或听音乐,正念冥想,运动,看书,讲笑话,看电影或看电视剧
通过小组讨论或单独聊天/发短信/facetime,与家人和朋友保持亲密关系,感受到亲情和支持
与社区建立联系:捐赠或接受捐赠,关注当地社区消息,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定位,生活在现实中
要限制看电视和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
如果因为日复一日地照顾病人,承受了太大的身心压力,与同事,朋友,治疗师或精神科医生交谈是个好主意。还可以找”雇员帮助”(EAP: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 )。各地还有热线电话和互助组
如果您或周围的同事朋友原有精神疾患加重,或COVID19 大流行触发了新的精神疾患,则必须寻求专业诊治。
蒋蔚医生, Director of Neuropsychocardiology
Internal Medicine, Psychiatry & Behavioral Sciences
Duke University Health System
怎么跟困难的病人和家属沟通
患者可能被标记为“difficult”:
人际交往的“困难”
精神心理疾病
慢性病,尤其是不依从医生管理的
缺乏社会支持,
患者会使医护人员感到恼怒,不适,无效或受到威胁,或者对治疗无反应
具有某些行为方面的患者被视为困难者
苛刻,责备,不欣赏,防御或愤怒
行为会导致滥用,暴力,自杀,诉讼或有向监管委员会报告的风险
这些困难患者的昵称:“火车残骸”,“缸”,“常客”和“心脏沉底”
精神科专家看到困难的患者可能有:
严重的精神疾病影响沟通
人格障碍
冲动控制不良
substance物质使用与否
躯体形式障碍
自毁倾向
适应不良的生活
应对不佳
患精神障碍的困难患者几率几乎是非困难患者的两倍(Hahn 1996)。
恐惧和焦虑是对危险的自然反应,包括我们所听到的危险或我们的想象力所产生的危险。为了保护我们免受伤害,有一点恐惧是必要的,因为它会导致下丘脑激活交感神经系统和肾上腺皮质系统,将它们结合在一起。产生战斗或逃跑反应fight or flight的效果。这种反应增加了葡萄糖的含量,为肌肉提供了能量,并暂时关闭了一些不必要的系统,使身体的全部精力集中于产生紧急反应。
困难患者对专业人员的情感影响可能很强,从而引发焦虑,悲伤,愤怒,羞耻,倦怠,无能为力,疲惫或被操纵的感觉。
把困难变成一种挑战!
Don’t Take It Personally 别往心里去!(只要记住这点,讲座就没白听了)
Show That You Care (放低姿态,然后说by the way, 这个问题那个问题)
Stay Calm (深呼吸,不能被激惹)
Know Our Own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Don’t Accept Abuse (不要忍气吞声)
跟病人沟通技巧:empathy (共情),non judgemental listening (不要主观偏见或者先入为主), patience and tolerance (耐心和忍耐), direct approach (不要啰嗦), define limits of time and content (不要无边无际), referal (转诊)
Confrontation with the patient (该说就说,但要有技巧)recommendation transfer (必要时可以换医生), humor, involve family, share some doctor’s personal experiences, ignoring patient’s feeling (忽略病人的不尊重,不要对小的事情斤斤计较)
跟病人家属的沟通:
每天跟家属沟通15分钟,紧急事件一定及时沟通。
提前约好沟通时间,如果家属不出现,当天不再提供时间沟通。
最好面对面沟通,尤其是第一次。电话效果差些。
整个梯队口径一致。要设置和遵守界限boundaries and limits。
程璞医生 Indiana Inpatient director
Grassroots 互助组织 --美国
TOPGUN project (针对武汉)成立于2020年1月24日,即武汉被禁的第二天。这是一个致力于帮助武汉一线医护人员的跨学科团队。CBT /动机面询/危机干预,一共45名成员,全部是中英文流利的有执照的精神卫生专业人员(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获得许可),包括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顾问,治疗师和注册护士。大多数成员位于北美,除了澳大利亚1个,武汉1个。
工作原则是不要伤害,保密,把这项工作局限于同行的支持(不是病人医生关系),短期危机干预。没有利益冲突(没有政治或金钱考虑)
用微信建立2个聊天组。第一组:成员办公室,第二组:进行干预的地方,300名当地医护人员每天可以聊天(大组里或者私信),志愿者成员轮流值班,每天总共提供16小时的服务。在进行个人干预之前都已获得对方同意。大多数寻求帮助的是医生(58%), 护士 (26%)。反馈比较好,觉得这个小组帮助他们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中国武汉的医护人员所经历的情绪阶段:困惑,震惊,愤怒,焦虑,倦怠,绝望,接受,希望,康复,后果。
受武汉TopGun项目启发,grassroots 组织(Physician support line-PSL)在美国成立了。通过facebook专业小组(COVID医生小组)招募了志愿精神科医生,5天内有300多名参加。3/23组织。管理团队由五人组成(包括程医生)。3/30正式开始展开工作。
目前发展成全国性的热线电话,已有600多名志愿精神科医生参与。
以下是联系方式:
Physician Support Line 1-888-409-0141 (7days a week, 8 am-12 am EST)
www.physiciansupportline.com
Q&A
1. How to self care in the midst of covid 19, especially managing the news of clients’ death and provide counseling to the family
Dr. Wu回答: 社工,医生,comfort team一起谈,可以打电话给家属汇报,直接而客气,告诉不好的消息。要有同理心。要注重自己的工作,生活尽量正常化,小心保护好自己,洗手戴口罩。
Dr. Jiang回答:因为病毒肆虐对病人的管理更困难了,象在伤口上撒盐。要劝人寻找精神心理方面的帮助(有的雇主提供这种服务),mindful 正念,打坐,让大脑平静下来,不想或者只想一件事。可以追剧来让大脑休息。给自己时间,每天要有十个小时注重于自己的身体精神健康,比如吃个葡萄干,观察一下自己的感受。要休息,睡好觉!参与正面的活动。沟通时要很谨慎,让病人知道我们在乎他。
2. PSL open to a physician in Canada?
Dr. Cheng 回答:目前只是针对美国。加拿大也在建立类似的组织,希望很快会有。
COVID-19 可导致格林-巴利综合症(GBS)
所谓新冠的命名其实已是过去式了,只是大家还是习惯性沿用着。现在国际正式命名应是冠状病毒病-2019 (COVID-19, 中文音译: 口服易得-19, 如何?医人版权), 英文全名是 cononavirus disese-2019. 引起COVID-19 的病毒是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冠状病毒2(SARS-CoV-2)。
为什么不叫做冠状病毒肺炎呢?笔者认为至少有几个原因:1) 有约25% 左右的病人是无症状的,没有肺炎;2)一部分轻症者只有轻微症状,也没有肺炎;3)更重要的是,目前为止,大家认识到COVID-19是全身性疾病,而不仅仅是呼吸道疾病。除影响呼吸系统外,病毒还可影响神经系统(中枢及外周),消化,心脏,肾,血液,皮肤等。
意大利帕维亚的IRCCS C.蒙迪诺基金会医学博士Gianpaolo Toscano,于4月17日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在线发表了5例COVID-19 相关的格林-巴利综合症(Guillain–Barré syndrome,GBS)的病例。这是继中国学者H Zhao 等4月1日在 The Lancet Neurology 在线发表首例COVID-19相关的GBS报告后更多的GBS病例报道。这5个病例进一步支持了该病毒与包括GBS在内的神经系统并发症之间的联系,不仅包括中枢也涉及外周神经系统。
顺便提一下,GBS是急性外周神经系统炎症,通常影响多个神经根及外周神经, 通常是由自身免疫攻击外周神经系统引起。
从2020年2月28日至2020年3月21日,Toscano等在意大利北部的三家医院检查了5名在Covid-19发作后患上格林-巴利综合征的患者。在此期间,估计有1000至1200名Covid-19患者入院。该系列中的四名患者在神经系统综合征发作时鼻咽拭子SARS-CoV-2阳性,一名患者鼻咽拭子阴性,支气管肺泡灌洗阴性,但随后对该病毒的血清学检测为阳性。补充附录中提供了详细的病例报告,该信件的全文可在NEJM.org上获得。
表格1
Covid-19发作后的5例格林-巴利综合征患者的特征。
四名格林-巴利综合征患者的最初症状是的下肢无力和感觉异常,面部瘫痪,其中一名患者出现共济失调和感觉异常(表1)。四名患者在36小时至4天的时间内发展为全身性松弛性四肢瘫痪或四肢瘫痪。三人接受机械通气。Covid-19症状发作与Guillain-Barré综合征首发症状之间的间隔为5到10天(所有患者均无自主神经功能异常)。
在分析脑脊液(CSF)时,两名患者的蛋白质水平正常,所有患者的白细胞计数均低于5/立方毫米。在接受测试的三名患者中均没有抗神经节苷脂抗体。在所有患者中,SARS-CoV-2的CSF实时聚合酶链反应测定均为阴性。
电生理研究的结果示于表S1中。
复合肌肉动作电位振幅低,但可以得到;两名患者的运动远端潜伏期延长。在肌电图检查中,最初有3位患者出现纤颤电位。在另一位患者中,纤颤最初时都未出现,但在第12天出现。这些发现通常与三名患者的格林-巴雷综合征的轴突变异和两名患者的脱髓鞘过程一致。磁共振成像显示两名患者的尾神经根信号增强,一名患者的面部神经信号增强,而两名患者的神经没有信号变化。
表S2列出了其他实验室检查结果。
所有患者均接受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IVIG)治疗。两人接受了第二次IVIG治疗,其中一人开始进行血浆置换。治疗后第4周,有2名患者留在重症监护室并接受机械通气,其中2例因松弛性截瘫而接受物理治疗,上肢运动极少,其中1例已出院且能够独立行走。
从病毒性疾病发作到GBS的最初症状的5到10天的间隔类似于在其他感染期间或之后发生的GBS的间隔。以前许多传染源如空肠弯曲菌,爱泼斯坦-巴尔病毒,巨细胞病毒和寨卡病毒与GBS相关的报道较常见。
根据对这五名患者的观察系列,尚无法确定严重病人的临床缺陷和轴突受累是否是Covid-19相关性格林-巴利综合征的典型特征。也无法确定是否这些患者呼吸衰竭是由于Guillain-Barré综合征引起的神经肌肉衰竭而导致肺活量降低,但如果胸部影像学检查结果与呼吸功能不全的严重程度不相符,则可以考虑这种关系。带有Covid-19的Guillain-Barré综合征应与重症神经病变和肌病应区分开,后者在危重病过程中比Guillain-Barré综合征出现的更晚。
尽管GBS病例很少见,但这些少见的病例有助于提高一线临床医生对GBS作为COVID-19潜在并发症的认识。
这5个意大利病例加上4月1日报道的一例中国病例进一步支持了COVID-19可引起包括GBS在内的神经系统并发症,不仅包括中枢神经系统也涉及外周神经系统。
Ref:
April 17, 2020
DOI: 10.1056/NEJMc2009191
Gianpaolo Toscano, M.D. - IRCCS C. Mondino Foundation, Pavia, Italy
Francesco Palmerini, M.D. - Istituto Ospedaliero Fondazione Poliambulanza, Brescia, Italy
Sabrina Ravaglia, M.D., Ph.D. - IRCCS C. Mondino Foundation, Pavia, Italy (sabrina.ravaglia@mondino.it)
Luigi Ruiz, M.D. - Azienda Ospedaliera SS. Antonio e Biagio e Cesare Arrigo, Alessandria, Italy
Paolo Invernizzi, M.D. - Istituto Ospedaliero Fondazione Poliambulanza, Brescia, Italy
M. Giovanna Cuzzoni, M.D. - IRCCS C. Mondino Foundation, Pavia, Italy
Diego Franciotta, M.D. - IRCCS C. Mondino Foundation, Pavia, Italy
Fausto Baldanti, M.D. - IRCCS Policlinico San Matteo, Pavia, Italy
Rossana Daturi, M.D. - IRCCS Policlinico San Matteo, Pavia, Italy
Paolo Postorino, M.D. - IRCCS C. Mondino Foundation, Pavia, Italy
Anna Cavallini, M.D. - IRCCS C. Mondino Foundation, Pavia, Italy
Giuseppe Micieli, M.D. - IRCCS C. Mondino Foundation, Pavia, Italy
Ref:
Guillain-Barré syndrome associated with SARS-CoV-2 infection: causality or coincidence?
Hua Zhao †
Dingding Shen †
Haiyan Zhou †
Jun Liu
Sheng Chen
Show footnotes
Published:April 01, 2020DOI:https://doi.org/10.1016/S1474-4422(20)30109-5
ANACP Covid-19讲座系列:一线PCP实战经验
ANACP北美抗疫Covid-19系列讲座:
一线PCP实战经验讲座报道
4/18/2020 周六
鲍亚群整理
张进医生:
张进医生是在纽约practice的PCP家庭全科医生, Affiliated Hospital: North shore university hospital和Long Island Jewish medical center。
她同时也在 Health Need Urgent Care 工作.
首先,张进医生给我们简单概括了从三月初到现在关于新冠病毒在美国发生发展的几个阶段,尤其是纽约政府采取的跟进应对方法,包括隔离建议,居家令。
然后她又具体的给大家分享了她亲自看诊的9个各有特点新冠病人的案例。有的有典型的发热,呼吸道系统症状;而有的就有非典型的发热腹痛消化道症状;有的属于中轻度症状,只需要门诊治疗;而有的病情比较严重,需要送到急诊室和医院治疗。
总结以上病例,张进医生有如下分享:
1)虽然有些常见症状:
fever, diarrhea, nausea, loss of smell and taste, short of breath, fatigue, Headache, throat pain,Bodyache, 新冠病人并不都有发烧。但是需要注意非典型病症,例如胃疼,肚子疼,尤其是老年人常见fever, Extreme fatigue, severe loss of appetite。
2)许多在家观察,多喝水,多吃营养食物,多洗热水澡,有可能康复。
3)Hydroxychloroquine虽然没有正式批准,但是在没有其他更好的治疗方案的时候,应该及时使用。有些病人不应该等待病毒检测结果,也等不及回家观察。有些患者从轻症到重症发展很快。
4)剂量Hydroxychloroquine 2tab 200mg BID day 1, 1tab 200mg BID 5days
Azithromycin 500 mg PO one day, 250 mg PO four days
Doxycycline 100 mg po, 7-10 days
Albuterol Neb tx
Prednisone 10-15mg
5)有时考虑另外一个药物组合:HCQ + doxy, 避免HCQ+z-pack两个药都有QT延长的副作用。
6)3/17-4/18 一共有61位患者使用了 Hydroxychloroquine,没有一例显示明显副作用,这些患者中,也无人发展成重症需要插管。但如果不及时给药,许多人都有可能发展到ER去。
7)曾有报告武汉医生进入重症病房之前,会提前两星期使用HCQ。印度也有类似情况,医生自行提前服用。
8) Zinc was shown to reduce the duration of common cold and inhibit the activity and replication of another coronavirus (SARS-CoV which caused an outbreak in 2002) in the laboratory.
因此,有些中国医生,还有其他国家的医生把zinc 加入对COVID-19 的治疗中。许多止咳药物甚至食物,比如cereal中都有。
9)鼓励病人使用热水澡,即使疲乏虚弱,也应该尝试。有报道做热瑜伽、桑拿的病人发展重症新冠肺炎的不多。
10)目前门诊病人中有80到90% 的是新冠阳性病人。奇怪的是,平时经常出现其他急诊病人如孩童等都不出现了。
11)许多出现在急诊室的新冠病人,通常已经是病情比较严重的了。即使有因其他病因而来,但在目前这个情况下,人人都应该考虑新冠阳性的问题。
周帆医生:
周帆医生在杜克的学生健康中心工作,她以自己诊所为例,分享PCP的工作情况和学习体会。1) 及时发现和分诊疑似病人,2)轻症病人在家隔离的时候,有效地监测和相应的对症治疗, 3)解除隔离的指征, 4)COVID流行期间, 照顾好其他病人,也同时保护好自己和诊所的医护人员。
1)如何及时的发现疑似病人并且正确的送捡。我们首先从主诉和症状开始。鉴于我们对这个新的疾病的认识, 是一个逐渐的学习和摸索过程, 虽然我们已经了解大部分COVID病人的症状, 但是总会有非典型的病人,会有一些非典型的症状出现。所以在COVID流行期间, 如果病人有非特异的症状表现,而不能用其他原因解释的,我们都要考虑排除COVID。 另一方面对于拥有非特异性全身症状的病人,因为其他的疾病也会有这些表现,如何在正确筛查COVID同时,在鉴别诊断的基础上,及时处理能够引起类似症状的其他疾病,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关注的方向。
由于COVID有些症状的非特异性,这个分诊无疑就增加了难度。她分享了杜克医疗系统里用的分诊流程。主要的思路,是注重病人的年龄和其他的基础疾病的询问,还有就是关于急性呼吸困难的分诊和及时送到急诊室。在急性呼吸困难排除以后,再根据病人是没有症状,轻度症状还是中度症状而建议居家隔离还是送到检测点。
2)病人确诊COVID阳性以后,轻症的会居家隔离。由 P C P办公室监测。一方面是症状方面的观察,主要是发热和呼吸系统症状症状的变化,这些跟以后解除隔离密切相关。另外一个症状的监测就是有没有呼吸困难,这个症状决定了病人可以继续居家隔离,还是需要送到急诊。还有一个监测就是病人的生命体征。在居家隔离的时候虽然有所限制,但是还是要尽可能的进行。生命体征的观察能够给我们更多的客观依据。例如体温,血氧,心率,血压的监测, 可以帮助我们在有限的条件下评估病人的感染进展。
在病人居家隔离时, 我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门诊COVID的治疗。大多数的都是对症治疗。比如用泰诺来降低体温, mucinex来帮助咳嗽。而咳嗽症状。相对而言有些迁延不愈,我们一方面跟病人解释咳嗽在呼吸道感染中确实是病情好转了还不一定消失。另外一方面寻找其他因素在里面,比如过敏,试试claritin,另外, 哮喘的病人,加用激素喷雾剂。在病毒感染的时候,有时候会合并细菌性感染,考虑加上z-pack. 还有一个药就是hydroxylchloroquine , 虽然没有确认的数据,这个对COVID有用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病很新,如果一定要等实验证据, 那么大家就等着束手无策了。所以这个时候,体现了我们作出临床判断的重要。在不引起损伤的前提下,考虑谨慎使用。
3)什么时候可以解除居家隔离。对于COVID 的轻症病人来说。一个标准是non-test base, 说的是退烧三天以后,呼吸道症状有所缓解,从症状发生第一天已经过去了七天。这是CD C给的指南, 北卡卫生部也是根据这个标准。但如果严格把关呼吸道症状明显好转这条标准,他们解除隔离的病人已经退烧七天,而距离他们第一次有症状也过了14天, 同时病人也很接受。第二种标准就是test based, 没有发热,然后呼吸道的症状有所提高,同时检测两次都是阴性的。但是由供应问题,大部分地区都没有按照这个标准来解除隔离。以后如果抗体的测试慢慢推广,可能就会有新的指南,根据抗体的测试来解除隔离。
4)COVID流行期间怎么照顾普通病人,同时也好好的保护自己诊所的医护人员。放宽远程医疗的条件,仅保留10%左右的on-site的病人。同时对诊所的感染防控规章制度更加严格地进行了调整。诊所整个大楼谢绝访客,所有的病人和工作人员进来就会发一个口罩。设立一 个专门的隔离通道和隔壁房间,以应对突发情况。为了保持社交距离, 员工都是轮流上班, 而且大家都特别注意整天的戴口罩和洗手。另外我整个诊所大楼的清洁也比以前严格得多。
总结体会:在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的时候怎么样利用临床判断来行医。在我们对什么事情所知不多的时候,不妨从我们已经知道的开始,从最基本的问病史查体,生命体征,鉴别诊断开始进行病人的监测和判断。而我们个人的经验都是有限的,如果我们把每个人所知道的一点点就像拼图一样拼在一起,大家互相分享,互相学习,相信这个拼图就会越来越完整。这也是我们北美华人医生联盟组织各地的医生进行经验分享和交流的目的,
Q/A:
1)关于biling/coding,in COVID period, new pt video visit 10min 用99201;20 min 99202, 以此类推。established video visit, 也可以根据时间用99213,99214等等。
2)门诊新冠病人比例?张80-90%; 周50%
3)关于HCQ的使用,张医生的经验是轻症-中症病人没有心脏病的都给了HCG。因为目前没有更好的方法。以前在使用这个药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多的担心。以前有给即将去非洲旅游的,都没有过多考虑QT问题。
4)听众询问了一个案例,某病人出现Unilateral infiltrate, 建议需要differentiate secondary bacterial infection, 考虑使用光谱抗生素。
5) 82yo positive COVID, 有AV block 不会给HCQ
ANACP does not endorse any conclusions and/or recommendations made by speakers during ANACP presentations and meetings held through third party conferencing entities.
ANACP does not warrant the safety, reliability, accuracy, completeness and/or usefulness of any information provided and is not responsible for any damage that may result from this presentation.
文中观点也不代表美国医人公众号意见。
ANACP北美抗疫新冠系列讲座链接:
JAMA:COVID-19 呼吸窘迫的处理
JAMA:COVID-19 呼吸窘迫的处理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可以起源于肺泡的气体侧或血管侧。尽管冠状病毒病-2019(COVID-19)的入侵门户是吸入性的,并且肺泡浸润通常在胸部X射线或计算机断层扫描(CT)扫描中可发现,但呼吸窘迫似乎包括一项重要的血管损伤, 这种血管损伤可能需要采取与常规ARDS处理的方法不同的治疗方法。的确,不同重症监护病房的死亡率差异很大,这有可能是因为通气管理方法得不同所导致的。
COVID-19是一种主要损伤血管内皮的全身性疾病(COVID-19 is a systemic disease that primarily injures the vascular endothelium)。如果不考虑血管中心特征对患者进行专业和个性化的治疗,即使是非老年人或没有合并症的COVID-19 ARDS患者(COVID-19 patient with ARDS=“ CARDS”)也可能最终发展为多器官功能衰竭。
给ARDS病人通气的标准方法
通常,ARDS的特征是非心源性肺水肿,与分流相关的低氧血症和通气肺尺寸减小(“婴儿肺”),这导致呼吸顺应性低。在这种情况下,通常通过使用高水平的呼气末正压(PEEP),募集动作和俯卧位来实现募集先前塌陷的肺单位来增加肺的大小。由于较高的跨肺压力会导致整个肺部应急,ARDS肺对后者的耐受性很差,因此相对较低的潮气量以及对中度(允许)高碳酸血症的耐受性,有助于将呼吸机诱发的肺损伤( ventilator-induced lung injury ,VILI)降至最低程度。确实,在ARDS的早期阶段,在患者疲劳或接受镇静剂之前,与自发剧烈吸气导致的的高穿肺压可能会造成这种损伤(所谓的患者自发性肺损伤,patient self-induced lung injury [P-SILI])。
CARDS的临床特征
COVID引起呼吸窘迫后不久,尽管氧合非常差,患者最初仍保持相对良好的肺顺应性。分钟通气通常具有很高的特征。浸润的程度通常有限,最初通常以CT上的玻璃样图案为特征,表明是间质性水肿而非肺泡水肿,许多患者没有出现明显的呼吸困难。
在简化的模型中,可以将这些患者称为“ L型”,其特征是低肺弹性(高顺应性),CT扫描估计的肺重量轻和对PEEP的反应低。对于许多患者,该疾病可能稳定在此阶段而不会继续恶化。
而其他的病人(可能由于疾病的严重程度和宿主反应或管理欠佳)可能会转变为更具典型ARDS特征的临床表现。这些可以被定义为“ H型”,特征是具有广泛的CT consolidation,高弹性(低顺应性),较高的肺重量和对PEEP反应好。
显然,L和H型是两个极端,之间还包括中间阶段,它们的特征是L及H 的特点重叠。
另一个特征是高度激活的凝血级联反应,在肺部和其他器官中普遍存在微血栓和大血栓(图1);血清D-二聚体 (D-Dimer)水平非常高与不良预后相关。
这些观察结果表明,不对称的内皮损伤导致破坏肺血管调节,通气-灌流失调(最初的低氧血症的主要原因)并促进血栓形成。此外,如果不加以制止,呼吸驱动力显着增加,可能会加剧患者施加于高度脆弱的组织的呼吸作用而引起的潮气压力和能量负荷,从而在肺部炎症性发作中增加P-SILI 。在快速发展的环境中,只有公认的ARDS肺保护方法的某些方面在这些不同阶段仍然是合理的。更重要的是,对血管侧注意力不足(例如,避免体液过多,心输出量需求减少)可能会无意中促进适得其反的反应(例如,水肿)和医源性损害。
保护CARDS肺
具有良好肺部顺应性的L型CARDS患者接受的潮气量(通常为ARDS规定的潮气量)为7-8 mL / kg,而不会增加VILI的风险。实际上,对于一个体重为70公斤的人,其呼吸系统顺应性为50毫升/厘米水,PEEP为10厘米水,潮气量为8毫升/公斤,产生的平稳压力为21厘米水,驱动压力为11厘米水,两者均远低于目前公认的VILI保护阈值(分别为30和15 cm H2O)。较高的VT可以帮助避免因换气不足而减少潮气量而导致的重吸收性肺不张和高碳酸血症。
这个早期阶段的关键问题是血管调节功能受损,在这种情况下,正常的因缺氧而引起的肺血管收缩由于内皮损伤而无法发生,这会导致通气-血流失调,并导致严重的低氧血症。临床医生对Fio2的最初反应可能确实很早就被证明是有效的。如果不充分,则无创支持(例如高流量鼻O2,CPAP,Bi-PAP)可稳定轻度病例的临床进程,前提是患者不要施加过多的吸气努力。但是,如果通过给予氧气和无创支持不能降低呼吸驱动力,则持续强大的自发吸气努力会同时增加组织压力并增加肺部跨血管压力,血管流量和体液渗漏(即P-SILI)。然后可能很快出现肺功能(VILI漩涡)进行性恶化。早期插管,有效镇静和/或瘫痪可能会中断该周期。以较低的PEEP(8-10 cm H2O)为目标是合适的。通过较高的PEEP或吸气-呼气比反转来提高平均跨肺压,会使血流从过度张开的空域重定向,加重高渗透性微血管的压力,并损害CO2交换,而不会广泛招募功能性肺单元。
如果由于疾病本身和/或P-SILI而导致L型患者的肺水肿增加,则婴儿肺进一步缩小,并且H型表型逐渐发展。将整个通风工作量集中在已经负担过重的婴儿肺部上会增加其力量暴露和血流量,从而增强其进行性损伤的可能性。
导致婴儿肺部收缩的VILI旋涡有两个主要因素:空域 VILI 和灌注血管的应力增加(图2)。
随着时间的流逝,叠加的VILI和未经检查的病毒性疾病会引起炎症和水肿,从而促进局部和全身性血栓形成,强烈的细胞因子释放,右心室超负荷和全身器官功能障碍。在这种晚期状态下,建议采用更常规的肺保护策略:更高的PEEP(≤15 cm H2O),更低的潮气量(6 mL / kg)和俯卧位,同时将氧耗降至最低。无论哪种类型疾病,渐进脱机都应谨慎(表)。
COVID-19会导致独特的肺损伤。将患者分类为具有L型或H型表型可能会有所帮助。采取不同的通气方法,具体取决于患者的基础生理状况。
April 24, 2020
Management of COVID-19 Respiratory Distress
John J. Marini, MD1; Luciano Gattinoni, MD2
Author Affiliations Article Information
JAMA.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4, 2020. doi:10.1001/jama.2020.6825
JAMA: COVID-19抗体检测的前景和危险
3月下旬,随着冠状病毒病-2019(COVID-19)在全球肆虐,数百名科罗拉多州圣米格尔县(San Miguel County)居民进行了血液检查。他们站在学校体育馆(Telluride school gym)外,彼此相距6英尺排队等待着抽血,这个血液检测结果将会告诉他们是否已曾被病毒感染过了,是否已对严重的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冠状病毒2(SARS-CoV-2)产生了免疫反应。
这是美国的第一个此类社区范围内的活动,圣米格尔县卫生局在2周内为该地区8000名居民中的大多数自愿者提供了筛查。在3月26日和27日测试的986例中,只有8位对SARS-CoV-2抗体呈阳性反应。另外23个处于临界点,这表明它们最近已暴露于该病毒,并且刚刚开始产生针对该病毒的抗体,但是那是较早的情况。上面的检查将会重复一遍,以查看人群中抗体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花费将由由测试制造商联合生物医学公司和该县联合支付。
与聚合酶链反应(PCR)测试(也称为基于分子或核酸的测试)不同,抗体测试并非旨在识别活动性SARS-CoV-2感染。抗体测试不是去检测喉咙或鼻拭子中的病毒遗传物质,而是检测免疫反应的标志物-对于大多数人,在开始感到不适一周以上后,当症状已经消失时,IgM和IgG抗体会在血液中出现。
血清抗体测试不仅可以在事后确认可疑病例,还可以揭示谁被感染过, 包括无症状感染者。由于有轻度或无症状,多达四分之一的SARS-CoV-2感染者可能不经意地传播了病毒给别人。
西奈山伊坎医学院(Mount Sinai’s Icahn School of Medicine)的微生物学家弗洛里安·克拉默博士(Florian Krammer)在接受采访时说,这可能会对医疗保健工作人员产生重大影响。“如果我们从血清学上发现您是免疫的,则极不可能再次感染,这意味着您无法将病毒传播给您的同事或其他患者。而且,如果您必须接触COVID-19患者, 知道自己对感染有免疫力,那么自己也会更放心。”
抗体测试正在迅速地发展,包括Krammer团队和荷兰团队在内的学术研究人员越来越多地购买商业试剂盒和测试方案。科学家们说,这些测试将在未来几周和几个月内变得至关重要,届时它们可能会用于疾病监测,治疗,重返工作岗位的筛查等。他们也补充说,但是必须适当地部署使用测试,并且要承认尚未解决的关于抗体问题。
将抗体转化为治疗用
血清学测试第一个治疗应用将是筛选供血中的SARS-CoV-2抗体,然后,将含有来自康复患者的抗体的称为恢复期血浆输给重症患者。3月下旬在JAMA上发表的几例中国患者的早期结果令人鼓舞。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正在协调一项全国性的努力,以开发基于血液的,富含抗体的COVID-19治疗方法。它们包括恢复期血浆和由其衍生的超免疫球蛋白,理想情况下,它们将为接触该病毒的病人提供被动免疫。
纽约市西奈山卫生系统病理学部门主席卡洛斯·卡登-卡多(Carlos Cordon-Cardo)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说,作为FDA扩大访问计划FDA expanded access program的一部分,他们那里的医生已经开始将恢复期血浆输注到重症患者。克莱默(Krammer)的研究小组开发了用于筛查捐献者血液抗体的测试方法。
他们最近在预印本文章中描述了他们的新检测方法(尚未经过同行评审)。该测试最早在患者首次出现症状后3天从血浆中检测到抗体。至关重要的是,它与已经在人群中传播的其它人类冠状病毒没有交叉反应,表明它是特异地针对SARS-CoV-2的。“我们的测试发现,基本上每个人都没有先天免疫,”克拉默说。“没有预先存在的免疫性。这样一来,就可以容易地区分感染者和未感染者。”
抗体测试也可能有助于解决接受恢复期血浆或超免疫球蛋白的潜在意外后果。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的医学和微生物学教授李·韦茨勒医师在接受采访时说,接受这些治疗的某些COVID-19幸存者可能无法获得自身产生的免疫力,所以他们有再感染的风险。血清学检查可用于在其恢复后检查其抗体状态;免疫力低或没有免疫力的人将是今后接种疫苗的主要候选者。
西奈山(Mount Sinai)和联合生物医学(United Biomedical)的测试都是酶联免疫吸附检测(ELISA),这是一种可以测量抗体滴度的通用实验室平台。能够定量抗体对于鉴定具有丰富效价的恢复期血浆供体和研究免疫系统对病毒的反应非常重要。“我们在ELISA中测得的滴度似乎与中和抗体有关,” Krammer说。“因此,基本的想法是这些抗体滴度越高,受到的保护就越好。”
Krammer已与美国约150个不同的临床实验室共享了他的测试试剂和工具包。波士顿医学中心的传染病医生韦兹勒说,这类定量测试将帮助科学家了解病人需要保护的抗体类型或所需阈值。
但是,大量新的商业COVID-19抗体测试都不是基于ELISA的。它们是侧向流动免疫检测(lateral flow immunoassay),只提供简单的阳性或阴性结果,而没有定量信息。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市梅奥诊所传染病血清学实验室主任Elitza Theel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些试剂盒便宜且易于使用,并且视其使用方式而定,可能有助于疾病监测。
总部位于帕洛阿尔托的Nirmidas Biotech是提供快速,即时医疗侧向血流分析的众多公司之一。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裁唐梅洁博士表示,该公司的一个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实验室及其他合作伙伴正在评估该测试的性能。她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我们计划与医院,诊所,卫生保健和医疗机构合作,以验证测试并使其广泛可用。”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Poway的Diazyme实验室已经开发了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从概念上讲,它比侧向流动分析法更接近ELISA。测试产生与SARS-CoV-2 IgM抗体成比例的光信号。联合创始人兼董事总经理 Chong Yuan, PhD, 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该公司将在下个月向临床实验室运送约200万项测试盒。
在正确的时间进行正确的测试
4月1日,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对北卡罗来纳州研究三角公园的Cellex Inc.公司进行的SARS-CoV-2 IgG和IgM横侧向流动快速测定法给予了紧急使用许可(EUA)。两周后,西奈山的测试也通过了EUA。
到4月初,该机构还允许70多家公司未经此授权出售COVID-19抗体测试,尽管有一些条款限制。除其他要求外,没有EUA的制造商必须声明,他们已使用来自PCR确诊的患者的标本进行临床验证。检测报告必须注意,FDA尚未审查这些检测方法,并且不应将其用作诊断或排除SARS-CoV-2感染或告知患者感染状况的唯一依据。
然而,根据Theel的说法,有几家公司正在将侧流分析作为快速的即时检验来推销,以鉴定出有效的COVID-19,而FDA宣布将采取行动。“我们目前还不知道这些检测的效果如何,” Theel在一封后续电子邮件中说。
尽管商业制造商声称他们的测试具有很高的灵敏度和特异性,但他们尚未发布具体数据。赛尔说,缺乏透明度令人担忧:“问题是,在症状发作后,是否收集了这些样品以表明其敏感性和特异性?”
她的实验室发现,大多数SARS-CoV-2患者直到症状发作后至少11至12天才开始产生抗体或进行血清转化。她说:“因此,如果我们在护理时使用这些快速侧向流动分析来测试近期有症状的患者,……他们很有可能会是阴性结果。”
据新闻报道,FDA将对抗体测试进行广泛的监督。此外,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一位发言人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世界卫生组织(WHO)正在与合作伙伴及其自己的全球实验室网络合作,以评估可用于诊断和研究目的的检测方法。这项工作的一个合作伙伴是创新诊断基金会(FIND),这是一家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非营利组织,致力于评估PCR和血清学检测。截至4月中旬,该小组已选择27项抗体测试(主要来自中国)进行第一轮评估。测试的性能结果将在可用时发布在FIND网站上。
据新闻报道,新近可用的快速即时PCR检测,例如最近雅培(Abbott Laboratories)宣布的5分钟检测,不会在短期内大幅提高诊断检测能力。面对令人难以置信的需求中的PCR测试短缺,卫生系统可能会考虑将血清学测试作为替代诊断。但是专家强烈强调,通常不应将抗体检测用于诊断正在感染的病例。
Krammer说,用抗体测试来诊断活动性感染是“完全滥用”。抗体测试不仅可能会在早期报告假阴性,而且还会错过因免疫力低下而不产生抗体的人病人的感染诊断检测。
Theel说:“分子检测仍将是有症状患者诊断COVID-19的首选方法。”在她看来,抗体检测对活动性感染的唯一适当用途可能是对于症状已超过一周但PCR阴性的人。但确切的检测时间尚未确定。
Theel说:“我认为了解血清学检测的局限性非常重要,要认识到需要花费时间来建立可检测的免疫反应并使用它们进行检测的正确理由。” “具有复制和传播病毒的急性症状患者的血清学阴性结果会严重危害公共健康。”
复工
圣米格尔县公共卫生部门表示,将使用其检测结果在社区中检测和围堵COVID-19,并提供该病在该地区的流行情况的更清晰的情况。其他领域可能很快就会跟进:联合生物医学联合创始人兼当地居民Mei Mei Hu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正在计划在其他社区进行筛查。
编者:在作者发表本文后,Bendavidd 等在2020年4月3-4日,使用侧流免疫分析法对加州圣克拉拉县(Santa Clara County)居民的SARS-CoV-2抗体进行了SARS-CoV-2抗体的血清阳性率测试。在3,330人的样本中报告了针对SARS-CoV-2的抗体的流行程度,并针对邮政编码,性别和种族/民族进行了调整。结果在圣克拉拉县未经调整的SARS-CoV-2抗体阳性率为1.5%,人口加权患病率为2.81%。在三种测试性能特征情景下,圣克拉拉的COVID-19人口患病率从2.49%-4.16%。这些结果表明到4月初,圣克拉拉县的感染人数估算应介于48,000至81,000,比现今确诊的病例数多50-85倍。结论是在圣塔克拉拉县感染的范围比确诊病例数所表明的要多得多。其它地区,或其它国家也应有类似的存在。
政府官员和卫生系统需要准确的感染计数才能了解COVID-19的传播情况,进行接触者追踪,提出公共卫生建议并为医疗保健激增做准备。尘埃落定后,流行病学家将使用广泛的血清监测数据来更准确地估计感染该病毒的人数中有多少人得了重病或死亡。
为此,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抗体调查正在招募来自全国各地的10 000名志愿者,据新闻报道,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资助的血清调查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开始。同时,世卫组织正在为各国提供血清流行病学研究的早期方案和技术支持,并正在开展一项名为SOLIDARITY II的多国抗体测试研究。
至关重要的是,许多人认为,从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和紧急情况第一反应者开始,抗体测试还可用于使有免疫力的人返回工作或将其继续留在工作。Krammer建议,例如,为养老院配备有免疫的工作人员可以降低他们的高病死率。
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白宫冠状病毒特别工作组顾问安东尼·福西(Anthony Fauci)医师4月8日在JAMA直播表示:“血清监测将在……恢复正常的框架中发挥重要作用”。两项重要的COVID-19路线图-一个来自前FDA主任Scott Gottlieb,医学博士,另一个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Ezekiel Emanuel,医学医学-路线图,包括广泛的抗体测试,这是重新开放社会的关键一步。
“我认为,如果免疫力在增强,并且说我们有50%的人对此具有免疫力,那么这种病毒传播的机会就大大减少了,”医学博士Melanie Ott说道。旧金山格拉德斯通病毒学和免疫学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在某一时刻,我们将能够通过可能需要采取的最少额外措施将这种风险降至最低。”
沿着这些思路,媒体报道说,德国和意大利的研究人员将进行和研究大规模抗体检测,德国计划颁发“免疫证明”,以使其公民摆脱封锁。为国家卫生局提供基于证据的支持的英国公共卫生局最近讨论了全国性抗体筛查计划,该计划将在评估了正在考虑的快速在家里自己手指点刺测试的准确性后开始。截至发稿时,白宫尚未宣布类似计划。
根据人们的抗体状况,允许人们重新返回社会是假定过去的感染可以防止再感染,研究人员说这是可能的,但尚未明确。奥特说:“这种免疫反应的广度,持续时间和有效程度尚不清楚。”
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将努力在实验室中以及通过跟踪康复的患者以查看是否发生再感染来了解对病毒的免疫会给予何种保护性。到目前为止,新型冠状病毒似乎并没有快速突变。Wetzler说,这再加上其他病毒感染的经验表明,SARS-CoV-2抗体患者可能至少会受到保护。
但是,还有另一个潜在障碍。即使抗体产生后,个体也可以是PCR阳性的。“问题是,我们正在检测的是活病毒吗?它在复制吗?而且可以传播吗?我认为,在这一点上,这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Theel说。将阳性抗体测试与阴性PCR结果相结合可以减少仍然具有传染性的人们重新返回社会的机会。
最终,抗体阳性试验可能是一种摆脱隔离的通行证。克拉默说:“从长远来看,为整个人群提供这种疫苗会很好,因为每个免疫的人都可以从根本上恢复正常生活,因为他们无法感染其他任何人。”
他也告诫说,目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可能尚未在美国普通人群中广泛传播,而目前只是在“大规模流行开始”之时。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受到感染和免疫,他们可以通过重新上班来帮助推动经济发展。他们还可以为容易受到严重感染的人提供实际支持,可能直到疫苗到来为止。
4月初,Cordon-Cardo说,西奈山可能会将其检测方法的使用范围从实验性疗法扩展到测试卫生保健工作者。在Mayo诊所,临床抗体测试于4月中旬开始。如果这些应用之后是针对大众的广泛抗体测试的推出,那么它们可能会导致社会逐渐向由COVID-19改变的世界重新开放。
April 17, 2020
The Promise and Peril of Antibody Testing for COVID-19
Jennifer Abbasi
JAMA. Published online April 17, 2020. doi:10.1001/jama.2020.6170
JAMA: 冠状病毒病-2019(COVID-19)的药物治疗综述
摘要:
重要性:由新型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引起的冠状病毒疾病2019大流行(COVID-19)给鉴定有效的预防和治疗药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鉴于科学发现的快速发展和大量被SARS-CoV-2迅速感染的病人中产生的临床数据,临床医生需要有关这种感染的有效治疗方法的准确证据。
观察结果:目前尚无对该病毒有效的治疗方法。关于SARS-CoV-2病毒学的迅速发展为治疗提供了大量潜在的药物靶标。最有前途的疗法是瑞德昔韦(remdesivir)。体外,Remdesivir具有强大的抗SARS-CoV-2活性,但尚未获得FDA的批准,目前正在进行随机试验中。尚未证明奥瑟他韦(Oseltamivir)具有疗效,目前不推荐使用皮质类固醇。当前的临床证据不支持在COVID-19患者中停止使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
结论和相关意义:COVID-19大流行代表了这一代人最大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并且可能是自1918年流感大流行性爆发以来的最大危机。为调查COVID-19潜在疗法而开展的临床试验的速度和数量突显了这个需求:即使是在大流行期间,也要能够提供高质量的临床试验证据。迄今为止尚未显示出有效的疗法。
序言:
由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冠状病毒2(SARS-CoV-2)引起的新型冠状病毒病2019(COVID-19)的全球流行于2019年12月在中国武汉开始,并已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截至到2020年4月5日,在200多个国家/地区报告的病例超过120万,死亡69 000。这种新的Beta冠状病毒类似于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冠状病毒(SARS-CoV)和中东呼吸系统综合症冠状病毒(MERS-CoV)。基于其遗传亲缘关系,它可能起源于蝙蝠衍生的冠状病毒,并通过未知的中间哺乳动物宿主传播给人类。SARS-CoV-2的病毒基因组被快速测序,以进行诊断测试,流行病学跟踪和预防疾病的发展和治疗策略。
目前,尚无来自随机临床试验(RCT)的证据表明任何潜在的疗法可改善疑似或确诊COVID-19的患者的临床结果。没有临床试验数据支持任何预防性治疗。正在进行的临床治疗试验有300多项。这篇叙述性综述总结了有关针对COVID-19的主要建议的疗法(改用于实验性或实验性)的最新证据,并提供了该新型流行性冠状病毒的当前临床经验和治疗指导的摘要。
方法:
使用PubMed进行了文献搜索,以鉴定截至2020年3月25日发表的相关英文文献。搜索词包括冠状病毒,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冠状病毒2、2019-nCoV,SARS-CoV-2,SARS-CoV,MERS-CoV和COVID-19结合治疗和药理学。搜索结果共有1315篇文章。由于缺少RCT,作者还包括了病例报告,病例系列和评论文章。作者独立审查了标题和摘要以供收录。从引用的参考文献中可以找到其他相关文章。使用ClinicalTrials.gov网站上的疾病搜索词冠状病毒感染以及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中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研究索引,确定了正在进行的的临床试验。
SARS-CoV-2:病毒学和药物靶向:
SARS-CoV-2是一种单链RNA包膜病毒,通过病毒结构刺突(S)蛋白与靶向细胞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ACE2)受体结合。受体结合后,病毒颗粒利用宿主细胞受体和内涵体进入细胞。宿主2型跨膜丝氨酸蛋白酶TMPRSS2通过S蛋白促进细胞进入。一旦进入细胞,就会合成编码复制酶-转录酶复合物的病毒多蛋白。然后,病毒通过其依赖于RNA的RNA聚合酶合成RNA。合成了结构蛋白,从而完成了病毒颗粒的组装和释放。这些病毒生命周期的各个步骤为药物治疗提供了潜在的靶点(图)。
有希望的药物靶标包括非结构蛋白(例如3-胰凝乳蛋白酶样蛋白酶,木瓜蛋白酶样蛋白酶,RNA依赖性RNA聚合酶),它们与其他新型冠状病毒(nCoV)具有同源性。其他药物靶标包括病毒进入和免疫调节途径。表1总结了COVID-19的某些建议治疗或辅助疗法的作用机理和主要药理参数。
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
截至2020年4月2日,ClinicalTrials.gov上的搜索词COVID OR冠状病毒或SARS-COV-2导致351项有效试验,其中有291项特定于COVID-19的试验。在这291项试验中,约有109项试验(包括尚未进行的试验)招募,招募,活动或完成)包括用于治疗成年患者COVID-19的药物治疗。在这109项试验中,有82项是干预性研究,有29项是安慰剂对照试验。根据研究的描述,有11个4期,36个3期,36个2期和4个1期试验。22项试验未按阶段分类或不适用。
复选药品(Repurposed Drugs)回顾:
以前用于治疗SARS和MERS的药物可能是治疗COVID-19的候选药物。在SARS和MERS暴发期间,使用了多种具有明显抗SARS-CoV和MERS-CoV体外活性的药物,疗效不一致。对SARS和MERS治疗研究的荟萃分析未发现任何特定治疗方案的明显效果。下面,对一些最有前途的COVID-19改用药物的体外活性和已发表的临床经验进行了综述。
氯喹和羟基氯喹(Chloroquine and Hydroxychloroquine):
氯喹和羟氯喹在疟疾的预防和治疗以及包括系统性红斑狼疮(SLE)和类风湿性关节炎(RA)在内的慢性炎性疾病的治疗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氯喹和羟氯喹似乎通过抑制病毒进入细胞而进入细胞宿主受体的糖基化,蛋白水解过程和内涵体酸化。这些药物还通过减弱细胞因子的产生以及抑制宿主细胞中的自噬和溶酶体活性而具有免疫调节作用。氯喹在体外以较低的微摩尔范围的半数最大有效浓度(EC50)抑制SARS-CoV-2。羟基氯喹具有比氯喹对SARS-CoV-2(在体外生长24小时后)更低的EC50(羟基氯喹:EC50 = 6.14μM和氯喹:EC50 = 23.90μM)。
没有高质量的证据表明氯喹/羟氯喹治疗SARS或MERS的有效。来自中国的新闻简报报道说,氯喹已成功用于治疗100多例COVID-19病例,药物改善了放射学表现,增强了病毒清除率并缓解了疾病进展。但是,临床试验设计和结果数据尚未获得提交或发布以供同行评审,从而阻止了对这些声明的验证。
近期一项针对法国的36名患者(羟氯喹组20例,对照组16例)的开放标签非随机研究表明,与接受标准支持治疗的对照患者相比,每8小时口服200毫克羟氯喹可以改善病毒学清除率。在第6天,通过鼻咽拭子测量的病毒清除率羟氯喹为70%(14/20),而对照组为12.5%(2/16)(P = 0.001)。作者还报告说,与羟氯喹单药疗法(8/14,57%)相比,6例患者在羟氯喹中加用阿奇霉素导致病毒清除率更高(6/6,100%)。由迪迪埃·拉乌尔特(Didier Raoult)领导的一项关于COVID-19患者中羟氯喹和阿奇霉素联合使用的有争议研究于3月20日发表。
尽管取得了这些令人鼓舞的结果,但该研究仍存在一些主要局限性:样本量小(干预组仅20个,接受羟氯喹和阿奇霉素的仅6个);由于重病或药物耐受不良而导致治疗提前停止,从分析中剔除了羟氯喹组的6名患者;羟氯喹单药治疗和联合治疗组之间基础病毒载量不一样;尚未报告临床或安全性结果。这些局限性以及对联合疗法加重心脏毒性的关注,所以不支持未经其他进一步研究就采用该方案的建议。
迪迪埃·拉乌尔特(Didier Raoult)3月27日报道了同一名马赛团队的最新结果,在80位接受羟氯喹和阿奇霉素联合治疗的住院患者中,除一名86岁患者死亡和一名74岁仍在重症监护病房的患者外,其余所有患者的临床状况都有改善。用qPCR发现鼻咽病毒载量的快速下降。第7天的阴性率为83%,第8天的阴性率为93%。 第5天,97.5%的患者呼吸道样本病毒培养阴性。这使患者能够迅速
从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病房(平均停留时间为五天)转出。 与疾病自然进程相比,临床上有所改善。 其中有一例死亡,三名患者被转移到重症监护病房。
另一项前瞻性研究在中国对30名患者进行了随机分组,他们以1:1的方式将患者每天接受400 mg羟氯喹,5天加标准护理(支持性护理,干扰素和其他抗病毒药物)或标准护理的随机分组;病毒学结果无差异。在第7天,病毒学清除率相似,羟氯喹加标准护理组和标准护理组的清除率分别为86.7%和93.3%(P> .05)。目前,有几项研究氯喹和羟氯喹在COVID-19治疗中的作用的RCT。计划或招募医务工作者预防氯喹的研究(NCT04303507)和高危暴露后羟氯喹对暴露后预防的研究(NCT04308668)。
用于治疗COVID-19的氯喹的剂量为500mg每天一次或两次口服。然而,关于确保氯喹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最佳剂量尚缺乏足够的数据。治疗SLE的羟氯喹剂量建议一般为每天400 mg口服。然而,基于生理学的药代动力学模型研究建议,COVID-19治疗中羟氯喹的最佳剂量方案为400 mg负荷剂量,每天两次,连续1天,然后200 mg每天两次。相反,根据安全性和对Whipple病的临床经验,建议每日总剂量为600mg。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确定COVID-19的最佳剂量。
SLE和疟疾患者的丰富经验证明,氯喹和羟氯喹的耐受性相对较好。但是,两种药物均可引起罕见且严重的不良反应(<10%),包括QTc延长,低血糖,神经精神病和视网膜病变。建议在开始使用这些药物之前和之后进行基线心电图检查以评估QTc延长。心律失常的可能性,特别是在重症患者和同时服用QT间隔延长药物如阿奇霉素和氟喹诺酮类药物的患者中。在COVID-19的建议剂量和持续时间内,氯喹没有明显的不良反应报道。妊娠中使用氯喹和羟氯喹通常认为是安全的。一项对12项研究的回顾,包括588例在妊娠期间接受氯喹或羟氯喹的患者,未发现婴儿的明显眼毒性。
洛匹那韦/利托那韦(Lopinavir/Ritonavir) 和其他抗逆转录病毒药:
Lopinavir / ritonavir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的用于治疗HIV的口服联合剂型·,通过抑制3-胰凝乳蛋白酶样蛋白酶表现出对其他新型冠状病毒的体外活性。洛匹那韦/利托那韦SARS-CoV-2的体外试验数据尚未见存在。对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用于治疗SARS和MERS的系统评价发现这方面的研究有限,其中大多数研究是在SARS上。SARS的临床研究与降低死亡率和插管率有关,但其回顾性和观察性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在病毒复制高峰期的初期(最初的7-10天)给药的时间似乎很重要,因为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的延迟治疗对临床结果没有影响。
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用于治疗COVID-19的早期报道大多是病例报告,及小型回顾性,非随机队列研究,这使得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的直接治疗效果难以确定。最近,Cao及其同事报道了开放性RCT的结果比较了洛匹那韦/利托那韦与标准治疗在199例COVID-19患者中的疗效。重要的是,从症状发作到随机分组的中位时间为13天(四分位间距[IQR],11-16),组间无差异。两组患者的临床改善时间的主要结果是按7类序数标准或医院出院的2分改善来定义的(两组分别为16天[IQR,13-17]和16天[IQR,15-17]) ;危险比[HR]为1.31 [95%CI,0.95-1.85];P = .09)。此外,未观察到病毒清除率或28天死亡率的显着差异(19.2%对25.0%;绝对差异为-5.8%[95%CI,-17.3%至5.7%])。尽管延迟治疗开始可能部分解释了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治疗COVID-19的无效性,但亚组分析并未发现在12天内接受治疗的患者临床改善时间更短(HR,1.25 [95%CI,0.77-2.05 ])。尽管仍在继续接受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的其他RCT,但目前的数据表明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在COVID-19治疗中作用有限。
用于COVID-19治疗的最常用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给药方案为每天400 mg / 100 mg两次,最多14天。鉴于显著的药物-药物相互作用和潜在的药物不良反应(总结于表1中) ),如果使用了这种药物,则需要仔细检查相关药物并进行监测。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的不良反应包括胃肠道不适,例如恶心和腹泻(高达28%)和肝毒性(2%-10%)。在COVID-19的患者中,联合治疗或病毒感染可能会加剧这些不良反应。大约20%至30%的患者在出现COVID-19症状时转氨酶升高,最近的一项RCT显示,大约50%的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患者出现了不良反应,而14%的患者由于胃肠道不良反应而中止了治疗。引起的转氨性炎特别引起关注,因为它可能加剧由COVID-19引起的肝损伤。重要的是,在一些COVID-19研究试验中,丙氨酸转氨酶升高是一项排除标准,这意味着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引起的肝毒性可能会限制患者用其他药物。
其他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包括蛋白酶抑制剂和整合酶链转移抑制剂,通过酶活性筛选被鉴定为具有SARS-CoV-2活性。体外细胞模型证明了darunavir具有抗SARS-CoV-2的活性。这些药物的在COVID-19的效果尚无人类临床数据,但中国正在进行darunavir / cobicistat的RCT研究.
利巴韦林(Ribavirin):
鸟嘌呤类似物利巴韦林抑制病毒依赖RNA的RNA聚合酶。它对其他nCoV的活性使其成为COVID-19治疗的候选药物。然而,其针对SARS-CoV的体外活性是有限的,并且需要高浓度以抑制病毒复制,因此需要大剂量(例如,每8小时口服1.2g至2.4g)和联合疗法。在先前的研究中,患者接受了静脉内或肠内给药。没有证据表明可吸入性利巴韦林可用于nCoV治疗,呼吸道合胞病毒的数据表明,与肠内或静脉内给药相比,吸入式给药无效。
对利巴韦林治疗SARS的临床经验的系统评价显示,在30篇研究中有26项没有结论性结果,其中4项研究表明由于不良反应(包括血液和肝脏毒性)可能造成的危害。在MERS的治疗中,利巴韦林,通常,与干扰素联合使用时,对临床结果或病毒清除率无明显影响。利巴韦林缺乏SARS-CoV-2的临床数据意味着必须从其他nCoV数据中推断其治疗作用。
利巴韦林引起严重的剂量依赖性血液学毒性。SARS试验中使用的高剂量导致超过60%的患者发生溶血性贫血。在最大的MERS观察性试验中也发现了类似的安全隐患,大约40%的患者接受了利巴韦林加干扰素的输血治疗。接受利巴韦林治疗SARS的患者中有5%转氨酶升高。利巴韦林也是已知的致畸剂,在怀孕期间禁用。
利巴韦林对其他nCoV的不确定性疗效数据及其实质毒性表明,其在治疗COVID-19中的价值有限。如果使用联合疗法,可能会为临床疗效提供最佳机会。
其他抗病毒药:
批准用于治疗流感的神经氨酸酶抑制剂奥司他韦Oseltamivir尚无抗SARS-CoV-2的体外活性的文献报道。在中国,COVID-19的爆发最初发生在流感高峰季节,因此大部分患者接受了经验性的奥司他韦治疗,直到发现SARS-CoV-2是COVID-19的病因才停用。目前的一些临床试验, 奥司他韦只是用于对照组。但一旦排除流感,该药物在COVID-19的治疗中不起作用。
Umifenovir(也称为Arbidol)是一种更有前途的抗病毒药物,具有针对S蛋白/ ACE2相互作用并抑制病毒包膜膜融合的独特作用机制。该药物目前在俄罗斯和中国被批准用于治疗和预防流感,并根据抗SARS活性的体外数据,对治疗COVID-19的兴趣日益增加。目前正在研究COVID-19治疗的剂量是每8小时口服200 mg的用于流感的剂量(NCT04260594)。在中国,使用umifenovir治疗COVID-19的临床经验有限。一项针对67名COVID-19患者的非随机研究表明,使用umifenovir治疗中位时间为9天与较低死亡率(0%[0/36]对16%[5/31])和较高的出院率相关。该观察数据无法确定umifenovir对COVID-19的疗效,但中国正在进行的RCT正在进一步评估该药物。
其它药物:
已经对干扰素-α和-β的nCoV进行了研究,证明了干扰素-β对MERS的活性。大多数已发表的研究报告了利巴韦林和/或洛匹那韦/利托那韦联合治疗的结果。与其他药物类似,延迟治疗可能会限制这些药物的有效性。鉴于体外和动物数据的矛盾以及缺乏临床试验,目前不建议使用干扰素治疗SARS-CoV-2。当前中国指南将干扰素列为联合治疗的替代方法。传统上使用的其他几种免疫调节剂非感染性适应症的证明具有体外活性或据称具有抑制SARS-CoV-2的机制,包括但不限于baricitinib,imatinib,dasatinib和cyclosporine。但是,尚无动物或人类数据可推荐使用对于COVID-19,是否给予已经服用其他适应症的患者保护,还有待观察。
硝唑尼特(Nitazoxanide)是传统的抗蠕虫药,具有广泛的抗病毒活性和相对良好的安全性。硝唑尼特已显示出针对MERS和SARS-CoV-2.58,59的体外抗病毒活性。该药作为SARS-CoV-2的治疗选择尚待进一步的证据支持硝唑尼特的抗病毒活性,其免疫调节作用和安全性。
甲磺酸卡莫司他(Camostat mesylate)是日本公认的治疗胰腺炎的药物,它通过抑制宿主丝氨酸蛋白酶TMPRSS2.3阻止nCoV细胞在体外进入。这种新机制为将来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药物靶标。
SARS-CoV-2利用ACE2受体进入宿主细胞。这一发现激发了关于ACE抑制剂和/或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是否可能潜在治疗COVID-19或相反使疾病恶化的讨论。这些药物上调ACE2受体,如果病毒进入增强,理论上可能导致更糟的结果。相反,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在理论上可以通过阻断ACE2受体提供临床益处。存在相互矛盾的体外数据,以确定这些药物在COVID-19患者中是否具有有害或保护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临床社区和行医指南建议对已经服用其中一种药物的患者可保持治疗。
某些研究性药物的回顾:
瑞德昔韦Remdesivir
Remdesivir(正式名称为GS-5734)是一种单磷酸盐前药,它会代谢为活性C-腺苷三磷酸核苷类似物。该试剂是在筛选具有抗RNA病毒(如冠状病毒科和黄病毒科)活性的抗微生物的过程中发现的。该药的研发表明,由于EC50低和宿主对Ebola病毒的聚合酶选择性低,在埃博拉病毒爆发高峰期间看到了希望。目前,由于广谱性,瑞姆昔韦是一种有前景的COVID-19潜在疗法,针对几种nCoV的强大体外活性,包括SARS-CoV-2的EC50和EC90值分别为0.77μM和1.76μM。在具有MERS-CoV的小鼠肺部感染模型中,瑞姆昔韦预防肺出血并降低病毒肺滴度超过了对照组。
在单剂量和多剂量1期临床试验中评估了雷姆昔韦的安全性和药代动力学。静脉输注3毫克至225毫克的耐受性良好,没有任何肝或肾毒性的证据。Remdesivir在此剂量范围内显示出线性药代动力学,并且细胞内半衰期大于35小时。多剂量给药后,发生了可逆性天冬氨酸转氨酶和丙氨酸转氨酶升高。目前正在研究的剂量是单次200毫克负荷剂量,然后每天输注100毫克。目前不建议调整肝或肾,但对于估计肾小球滤过率低于30 mL / min的患者,不建议开始使用。
瑞德昔韦的第一个临床用途是用于治疗埃博拉病毒。但是,已经有雷姆昔韦用于COVID-19成功的病例报道。评估雷姆昔韦在轻至中度或重度COVID-19患者中的安全性和抗病毒活性临床试验正在进行(NCT04292899,NCT04292730, NCT04257656,NCT04252664,NCT04280705)。特别重要的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赞助了一项自适应,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该试验将揭示瑞姆昔韦与支持治疗相比的有效性(NCT04280705)。由于预期会有随机对照试验的结果,可以考虑将这种药物用于治疗COVID-19。
从4月10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的报告和后续更新中获得的有关该药物功效的最新数据表明,该药物在对抗新型冠状病毒方面可能至少具有某些功效。研究显示,在对重度COVID-19病人进行的“同情使用”试验中,服用remdesivir的53例患者中有36例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临床症状,接受药物治疗的患者中有一半以上最终能够拔其氧气管。
值得注意的是,remdesivir目前尚未获得FDA批准,必须通过同情性用药(仅限18岁以下的儿童和孕妇),扩大使用范围或参加临床试验来获得。
法维拉韦Favipiravir
Favipiravir(以前称为T-705)是嘌呤核苷酸favipiravir呋喃呋喃糖基5'-三磷酸的前药。活性剂抑制RNA聚合酶,停止病毒复制。法维拉韦的大多数临床前数据均来自其流感和埃博拉病毒活动;然而,该药物还表现出了对其他RNA病毒的广泛活性。在体外,在维罗E6细胞中,favipiravir对SARS-CoV-2的EC50为61.88μM/L。
基于感染适应症的类型,已经提出了各种给药方案。与埃博拉和SARS-CoV-2.相比,针对流感的favipiravir EC50值较低,可能导致剂量变化,应考虑在剂量范围较高的剂量治疗COVID-19.69(建议使用加药剂量(每12小时2400到3000 mg×2剂),然后维持剂量(每12小时1200 mg到1800 mg)。半衰期约为5小时。尽管高剂量方案的不良事件情况有限,但该药具有轻微的不良反应,并且总体耐受性良好。目前可通过以下途径获得Favipiravir:日本用于治疗流感,但在美国没有用于临床。
据报道有限的临床经验支持使用favipiravir用于COVID-19。在一项前瞻性,随机,多中心研究中,将favipiravir(n = 120)与Arbidol(n = 120)进行比较,以治疗中度和重度COVID-19感染。在中度感染患者中观察到了在第7天的临床恢复差异(71.4%的法维拉韦和55.9%的阿比多尔,P = 0.019)。在重度或重度和中度(合并)组中未观察到显着差异。这些数据支持用RCT进一步研究favipiravir治疗COVID-19的功效。
辅助疗法
目前,在没有针对SARS-CoV-2的可靠治疗方法的情况下,COVID-19患者的护理基础仍然是支持性护理,从对行的的门诊治疗到全面的重症监护支持。然而,值得特别提及的3种辅助疗法是皮质类固醇,抗细胞因子或免疫调节剂以及免疫球蛋白疗法。
皮质类固醇
使用皮质类固醇的基本原理是减少宿主在肺部的炎症反应,后者可能导致急性肺损伤和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但是,这种益处可能会被不良副作用所抵消,这包括延迟的病毒清除和增加的继发感染风险。尽管COVID-19中皮质类固醇的直接证据有限,但对其他病毒性肺炎的结局进行回顾是有指导意义的。SARS和MERS患者的观察性研究报告表明皮质类固醇与生存改善无相关性,但显示出病毒在呼吸道和血液清除延迟有关。还与高血糖,精神病和无血管坏死在内的高并发症发生率有关。此外,2019年对10项对6548例流感性肺炎患者进行的观察性研究的荟萃分析发现,皮质类固醇与死亡风险增加相关(风险比[RR]为1.75 [95%CI,1.3-2.4];P <.001)和二次感染的风险高出2倍(RR,1.98 [95%CI,1.0-3.8]; P = .04 )。尽管人们仍在争论ARDS和败血性休克中皮质类固醇的疗效,但Russell及其同事认为,最有可能从皮质类固醇中受益的是那些细菌性而非病毒感染患者。。最近对中国201例COVID-19患者进行的回顾性研究发现,对于罹患ARDS的患者,甲基强的松龙的治疗与死亡风险降低相关(类固醇激素占23/50 [46%],而21/34 [62%] ;无;HR,0.38 [95%CI,0.20-0.72] .. 47。但是,作者指出,在该观察性研究中,可能存在偏差。。因此,皮质类固醇的潜在危害和尚未得到证实的益处提示,除非存在伴随的令人信服的指征,例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恶化或难治性休克,否则不要在RCT之外的COVID-19患者中常规使用皮质类固醇。
抗细胞因子或免疫调节剂
针对关键炎症细胞因子或先天性免疫应答其他方面的单克隆抗体代表了COVID-19的另一类辅助疗法。使用它们的理由是,肺和其他器官的重要器官损伤的根本病理生理是由放大的免疫反应和细胞因子释放或“细胞因子风暴”引起的。79IL-6似乎是这种失调的关键驱动因素80基于中国早期病例系列的炎症反应。因此,针对IL-6的单克隆抗体理论上可以抑制这一过程并改善临床结果。单克隆抗体IL-6受体拮抗剂Tocilizumab被FDA批准用于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治疗后的RA和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有了这一经验,托西珠单抗已被用于一小批严重的COVID-19病例,并有成功的早期报道。21例COVID-19患者的报告显示,通过改善呼吸功能,快速退热和成功出院,对91%的患者接受400 mg托珠单抗治疗与临床改善相关,大多数患者仅接受1剂治疗。35缺乏比较组限制了对药物特异性作用的解释,因此在获得更严格的数据之前必须谨慎。中国正在对COVID-19严重肺炎的患者单独或联合使用几种托西珠单抗的随机对照试验(NCT04310228,ChiCTR200002976),该药物已纳入当前的中国国家治疗指南中。
Sarilumab是另一种批准用于RA的IL-6受体拮抗剂,正在一项针对重症COVID-19住院患者的多中心,双盲,2/3期临床试验中进行研究(NCT04315298)。临床试验中的其他单克隆抗体或免疫调节剂在中国或在美国可以扩展使用的药物包括贝伐单抗(bevacizumab,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药物;NCT04275414),芬戈莫德(fingolimod,批准用于多发性硬化的免疫调节剂;NCT04280588)和依库丽单抗(eculizumab,抗体抑制终末补体;NCT04288713)。
免疫球蛋白疗法
COVID-19的另一种潜在辅助治疗方法是使用恢复期血浆或超免疫免疫球蛋白(convalescent plasma or hyperimmune immunoglobulins)。这种治疗的理由是,康复患者的抗体可能有助于游离的病毒和感染细胞的免疫清除。有报道称恢复期血浆的报道或方案可作为SARS和MERS的二线抢救疗法(salvage therapy)。2009年对93名H1N1甲型危重患者进行了一项前瞻性观察研究,其中20名接受了恢复性血浆,证明了恢复性血浆与不接受会降低死亡率(20%比54.8%;P = .01)。
作为2015年系统评价的一部分,Mair-Jenkins及其同事86对8项观察性研究进行了事后荟萃分析,其中包括714例非典或严重流感。尽管研究质量通常较低且有偏见风险,但给予恢复性血浆和超免疫性免疫球蛋白可降低死亡率(几率,0.25 [95%CI,0.14-0.45];I2 == 0%),危害相对较小。
从理论上讲,当病毒血症达到高峰且尚未发生主要的免疫反应时,这种疗法的益处将主要在感染的前7至10天之内产生。尽管目前的市售免疫球蛋白制剂可能缺乏针对SARS-CoV-2的保护性抗体,但随着全球COVID-19康复患者的增加,这种方法值得进一步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试验。的确,最近发表了中国首例报道的5例用恢复期血浆治疗的COVID-19危重病人的非对照病例系列。此外,中国武汉的3例COVID-19病人的病例系列在2000年接受了静脉免疫球蛋白的治疗。最近公布了5天剂量为0.3至0.5 g / kg / d的剂量。
2020年3月24日,FDA发布了指导原则,要求紧急研究新药的应用并筛选COVID-19康复血浆的捐赠者。早期的预印本报告还描述了针对共同表位的人单克隆抗体的临床前开发,以阻断SARS-COV-2(和SARS-CoV)感染。
预防这种病毒未来爆发的最有效的长期策略是开发具有保护性免疫力的疫苗。但是,在广泛使用疫苗之前至少需要12到18个月的时间。对SARS-CoV-2疫苗研究的全面综述不在本综述范围内。
当前的临床治疗经验和建议
除提及的少数临床试验外,已发表的临床治疗经验主要由描述性报告和来自中国及其他在大流行早期受到影响的国家的病例系列组成。因此,鉴于存在混淆和选择偏差以及人口统计,测试和治疗方法的变化,必须谨慎解释包括病死率的结果。表2总结了早期报告的COVID-19病例系列的临床严重性,并发症,治疗和临床结果。
当前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关于COVID-19患者临床护理的指南(截至2020年3月7日)强调指出,尚无针对COVID-19的特异性治疗方法,并强调推荐的感染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指南特别提到,除非有其他原因,否则应避免使用皮质类固醇。通过富有同情心的使用或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可以选择研究性治疗药物,特别是瑞昔地韦。
同样,当前的世界卫生组织(WHO)临床管理指南文件(截至2020年3月13日)指出“目前没有证据为确诊COVID-19的患者推荐任何特定的抗COVID-19治疗。”
指南强调了基于疾病严重程度的支持治疗的作用,从对轻度疾病的对症治疗到对ARDS的循证通气管理,以及对重症患者的细菌感染和败血症的早期识别和治疗。他们建议“在临床试验之外不要常规给予全身性皮质类固醇激素治疗病毒性肺炎”,并指出“研究性抗COVID-19疗法应仅在批准的随机对照试验中使用。”在这方面,世卫组织最近宣布了一项计划,即启动一项名为SOLIDARITY的全球“大型试验”,该试验具有务实的试验设计,根据当地药物的可用性,该试验将已确诊的病例随机分为标准护理或4种积极治疗组中的1种(雷姆昔韦,氯喹或羟氯喹,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或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加干扰素-β)。
下面为临床医生回答了有关COVID-19患者临床管理的常见问题:
1.是否已有确切证据表明有药物可以改善COVID-19患者的预后?
目前,尚无明确证明可改善COVID-19患者预后的药物。在观察性研究或小型非随机研究中,许多药物已证明对SARS-CoV-2病毒具有体外活性或潜在的临床益处。目前正在招募足够有能力的随机临床试验,以建立这些可能有效疗法的临床试验证据。
2.对于COVID-19的严重症状的患者,是否应用羟氯喹和/或阿奇霉素?
据报道,羟氯喹和阿奇霉素对COVID-19患者的临床益处来自媒体报道或少数参与者(<100名患者)的非随机试验。有或没有阿奇霉素的羟氯喹的益处已被非常有限地记录,特别是在重症患者。尽管这些药物单独或联合使用可能有效,但在广泛地使用这些治疗方法之前,需要通过随机临床试验来确定这些效果。
3.老年患者和那些因COVID-19患有严重疾病的高风险患者应该停止ARBs / ACE抑制剂吗?
主要机构和学会,包括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美国心脏协会,美国心力衰竭学会和美国心脏病学会,建议对已经为其他适应症正在服用的所有患者继续使用ACE抑制剂或ARB药物。目前,尚无人类证据表明使用这些药物与增加COVID-19风险或疾病严重程度之间存在联系。
4.免疫调节药物(例如IL-6受体拮抗剂或皮质类固醇)在治疗COVID-19患者中起什么作用?
鉴于免疫应答在COVID-19并发症中起着重要作用,评估该疾病中的免疫调节药物(例如IL-6受体拮抗剂)的疗效的临床试验正在积极的开展。对于以炎症标志物明显升高为特征的“细胞因子风暴”患者,尽管这些药物会增加继发感染的风险,但在临床试验中最好考虑使用IL-6受体拮抗剂。皮质类固醇的作用仍存在争议,世界卫生组织的现行指南不建议使用皮质类固醇,除非存在其他伴随症状,例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恶化或顽固性休克。但是,它们在重症COVID-19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患者中的作用应在临床试验中进一步研究。
5.哪些药物已被重新用于治疗COVID-19?
许多试剂显示出对新型冠状病毒,包括SARS-CoV-2的体外活性。小分子数据库筛选确定了成千上万的潜在药物。在这些潜在药物中,已经提出了用于治疗多种其他疾病状态(例如,HIV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几种改型药物,作为COVID-19的可能治疗选择。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和氯喹或羟氯喹是治疗COVID-19的最具临床证据的药物,无论是阳性还是阴性。迄今为止,可用的临床试验尚未证明这些药物中的任何一种具有明显效果。
6.是否有可用于治疗COVID-19的研究性药物?
Remdesivir可通过注册临床试验或申请紧急救助(emergency access)的方式给COVID-19感染的患者使用。在美国,有3项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 它们根据疾病的严重程度(例如中度与严重感染)和研究设计(例如安慰剂对照)进行了区分。可通过扩展的访问程序(expanded access program)申请紧急救助, 无法获得临床试验的站点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得药物。同样,对孕妇和年龄在18岁以下且确诊COVID-19且疾病表现严重的儿童,可通过个人同情使用(compassionate use)获得这种药物。Favipiravir目前在美国尚不可使用。
7.如何确定COVID-19的患者是否需要特定治疗或仅应接受支持治疗?
如果病人符合标准,应优先考虑参加临床试验。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对门诊稳定的患者或通过影像检查无氧气需求或肺炎迹象的患者则通常用支持治疗。有缺氧或肺炎迹象的患者,尤其是那些具有疾病进展风险因素(例如65岁以上,心脏或肺部合并症,免疫抑制)的患者,在讨论了低氧血症或肺炎的风险和益处后,可以考虑采用特定的COVID-19治疗患者并按照当地医院的治疗指导。
8.重新使用药物(repurposing medications,已批准治疗别的疾病)治疗COVID-19的局限性是什么?
已批准治疗别的疾病的药物的使用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收益(体外/临床证据)超过相关风险(药物不良反应)。使用改用药物的局限性之一是这些药物容易引起急性毒性。这种急性毒性可能超过特定抗病毒药的尚不确定益处。联合疗法增强的毒性(例如心脏或肝脏毒性)会带来潜在的额外风险,并且需要进行密切风险与获益分析。总体而言,缺乏明显好处的证据可能不足以证明重新使用药物的风险。对于有药物毒性高风险的患者以及不良事件可能会阻止其进入研究试验的情况,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ACE: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RB: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COVID-19:冠状病毒病2019; SARS-CoV-2: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冠状病毒2。
Ref:
Article Information
JAMA: 冠状病毒病-2019(COVID-19)的药物治疗综述
April 13, 2020
James M. Sanders, PhD, PharmD1,2; Marguerite L. Monogue, PharmD1,2; Tomasz Z. Jodlowski, PharmD3; et al
Corresponding Author: James B. Cutrell, MD, Divis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Geographic Medicine, Department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Texas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 5323 Harry Hines Blvd, Dallas, TX 75390-9113 (james.cutrell@utsouthwestern.edu).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April 3, 2020.
Published Online: April 13, 2020. doi:10.1001/jama.2020.6019
Author Contributions: Dr Cutrell had full access to all of the data in the study and takes responsibility for the integrity of the data and the accuracy of the data analysis.
JAMA: 美国的COVID-19大流行: 临床更新
自2020年1月20日在华盛顿州确诊美国首例冠状病毒病-19(COVID-19)感染以来,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美国各地已发现超过235000例病例(编者注:截至4月10日505,242例)。鉴于在扩大测试能力方面的挑战以及疑似病例(persons underinvestigation,PUI)定义的限制,病例的实际数量可能还要高得多(编者注:别的国家也一样)。
到3月17日,疫情已从华盛顿,纽约和加利福尼亚的几个孤立群集性病例扩展到所有50个州和首都哥伦比亚特区。截至4月2日,在美国已有超过5000例与COVID-19相关的死亡(编者:截至4月10日,在美国已有18,764例与COVID-19相关的死亡,读者也要注意是“相关的死亡”)。目前,全球总病例数超过100万,美国是报告病例数最多的国家,约占报告的所有感染病例的五分之一。
随着社区传播的牢固建立,美国流行病进入了指数增长阶段,新病例数与现有病例数成正比。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有足够的易感个体由于感染而变得免疫,或者采取严格的公共卫生措施或两者兼而有之为止。
病死率(Case Fatality)
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增加了疫情爆发中的不确定性,这就是病死率(case-fatality rate ,CFR),病死率定义为所有病例中死亡人数所占的百分比。目前,据报告全球死亡率(原作者可能混淆了,用的是mortality,编者认为应是病死率fatality)为4.7%,但各地差异很大,从意大利的高10.8%到德国的低0.7%。影响CFR的几个因素包括对病例总数的可靠估计。在美国的前140904例病例中,有1.7%死亡(病死率,编者:截至4/10 是3.7%)。但是,鉴于分母的不确定性,这不是可靠的CFR估算。例如,2月1日,中国武汉的粗略病死率报告为5.8%,而使用更可靠的新方法估算实际病例数,估算得出病死率为1.4%。
在未来几周内,美国医院的医疗服务能力将影响病死率。但是,要获得可靠的估计值,必须对总人口(分母)进行更好的近似估算,并且使用可推广到目标人口的统计抽样进行的血清调查等方法将为这些估计提供依据。
新的临床和流行病学见解
PCR总是阳性吗?阴性PCR的含义是什么?几种类型的测试可用于识别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冠状病毒2(SARS-CoV-2)。这些测试可分为2大类:基于分子诊断/聚合酶链反应(PCR)的测试和血清学测试。在临床,PCR的检测仍然是鉴定SARS-CoV-2的主要方法。由于缺乏诊断COVID-19的参考标准,因此未知诊断测试的敏感性和特异性(sensitivity andspecificity )。此外,样本收集不足可能会降低测试灵敏度。在一项针对5例患者的研究中,胸部计算机断层扫描结果(CT)支持COVID-19,且SARS-CoV-2的逆转录酶(RT)-PCR结果阴性的患者在随后的PCR检测中又呈阳性,这表明某些患者(例如,放射学检查结果相符)可能需要对从呼吸道多个部位采集的标本进行重复测试。
下呼吸道样本(例如微支气管肺泡灌洗)可能比鼻咽拭子更敏感。因此,必须强调的是,根据临床表现,RT-PCR阴性结果并不排除COVID-19。多种血清学检测处于发展的不同阶段。随着血清学检测的广泛应用,将有可能确定患者是否具有假阴性的PCR结果。
患者可以重新感染吗?来自中国和日本的报告表明,一些RT-PCR结果阴性后出院的COVID-19患者被重新收住院,并随后在RT-PCR上呈阳性反应。从现有信息来看,尚不清楚这些是否是真正的再感染,或在初次出院时测试是否假阴性。尽管其他冠状病毒显示出再次感染的迹象,但通常不会持续数月或数年。因此,他们不太可能是真正的再感染病例。恒河猴的一次挑战研究提供了一些令人放心的证据。在最初的SARS-CoV-2感染和病毒清除后,这些动物再次受到该病毒的攻击,但没有再被感染。尽管有关再感染的证据在不断报道,但是来自以前没有实质性季节性突变的病毒的最新数据和经验并不支持这一假设。
免疫能持续多久?当前,没有针对SARS-CoV-2的保护的有效免疫相关性证据,即抗体水平或与针对感染或疾病的保护相关的另一种免疫学标记。但是,在一项包括来自中国的82例确诊病例和58例可能的COVID-19病例的研究中,IgM检测的中位数持续时间为5天(四分位数范围3-6),而IgG的检测中位数为14天(四分位数)症状发作后10-18)。由于冠状病毒病-19爆发仅数月之久,因此没有长期免疫反应的数据。来自SARS-CoV-1的数据表明,IgG和中和抗体的滴度在感染后4个月达到峰值,随后在感染后至少3年内下降。
每个人都应该在公共场合戴口罩吗?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当前指南不建议在健康个体中常规使用医用口罩,并建议将口罩的使用范围限制于医护人员和护理COVID-19的人员。但是,该指南可能会被修改。无论如何,任何政策变更都应优先考虑医护人员使用口罩的情况。还应优先考虑其他有接触风险的人,例如急救人员和被监禁的囚犯。由于目前口罩稀缺,社区中的许多人已开始为自己和医护人员缝制口罩。配备N95防毒口罩是医护人员首选的医用口罩。但是,美国的供应非常有限。对于有症状的人,也建议使用医用口罩,以防止他们传播病毒。
支持该建议的理由来自于研究,这些研究发现,口罩在保护健康个体免受流感感染方面没有效果,同时也必要保存必需的医用供应。但是,流感研究的证据可能与COVID-19没有关系。例如,在一项系统评价中,发现口罩,特别是与其他措施(例如洗手)相结合,可有效预防SARS-CoV-1感染。此外,随着SARS-CoV-2症状前传播(无症状携带者)的证据不断增加,在有传播危险的个人中使用口罩可能有价值。
SARS-CoV-2如何传播?当前证据表明,SARS-CoV-2主要通过液滴(飞沫传播,直径为5-10μm的颗粒)传播。当感染者在咳嗽,打喷嚏和说话时散发含有病毒颗粒的飞沫时,就会发生人与人之间的传播。这些飞沫降落在另一个人的呼吸道粘膜或结膜上,通常在6英尺(1.8 m)的距离内,但可能更远。这些飞沫还可以沉降在静止或可移动的物体上,当它们被接触时(如手)可以转移给另一个人。病毒在固体表面的存活一直是讨论的重要课题。尽管数据很少,但现有证据表明该病毒在室温下可在无生命的表面上保持感染力长达9天。在高于30°C的温度下,此时间较短。好消息是,清洁和消毒可有效减少表面污染,所以在频繁接触区域清洁是很重要的。
在特定情况下,例如气管内插管,支气管镜检查,抽吸,将患者转到俯卧位或使患者与呼吸机断开连接(脱机),也会通过小于5μm的气溶胶( aerosols)传播。心肺复苏是另一种重要的气溶胶生成操作。
在最近一项对COVID-19患者的房间进行环境采样的研究中,许多常用物品以及空气样本均具有病毒污染的证据。在证据不一致的背景下,某些能产生病毒气溶胶的临床操作中,公共卫生机构(包括CDC)建议在涉及COVID-19患者的情况下采取空气传染预防措施(airborne precautions)。
什么时候可以取消社交距离措施?随着美国COVID-19案件和死亡人数呈指数增长,一些辖区已实施了社交距离措施( social distancing)。建模和实证研究表明,社交距离措施可以帮助减少感染总数,并有助于在更长的时间内,让传播病例分散,从而使卫生系统可以更好地管理更多激增的患者。但是,长期的社交距离会对身心健康和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减轻社交距离限制可能需要进行一些改变:首先,积极的检测程序将无症状和轻度病例,加上与主动接触追踪,早期隔离。以及接触者隔离。第二,必须着重减少家庭内传播。在武汉,特别是在初始阶段之后,大部分传播发生在家庭内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已经发布了防止家庭传播的指南,但并没有充分强调让感染者始终戴口罩的重要性。第三,即使是仅将重症监护病房住院治疗时间缩短20%至30%,也可以对卫生系统的能力产生实质性的好处。
什么时候可以提供疫苗?控制这种大流行的最终策略将取决于有否针对SARS-CoV-2的安全有效疫苗。但是,目前只有3种候选疫苗在1期人体试验中:信使RNA疫苗和2种基于腺病毒载体的疫苗。估计可获得初始疫苗的时间是2021年初至中期。
结论
随着COVID-19疫情在美国的蔓延,人们对该病的总体了解也有所增加,与几周前相比,现在可获得更多信息。但是,需要更多的证据,特别是对于公共卫生和临床干预以成功预防和治疗感染。即使在大流行期间,获取严格,可靠的数据并不是在分散大家的注意力,相反,准确地测量COVID-19的广度,疾病的严重程度以及评估反应的有效性是非常重要的。
Ref:
April 6, 2020
The COVID-19 Pandemicin the USA Clinical Update
Saad B. Omer, MBBS, PhD1,2; Preeti Malani, MD, MSJ3,4; Carlos del Rio, MD5,6
Author Affiliations Article Information
JAMA. Published online April6, 2020. doi:10.1001/jama.2020.5788
Article Information
Corresponding Author: Carlos del Rio, MD, Emory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49 Jesse Hill Jr Dr SE, FOB Room 201, Atlanta, GA 30303 (cdelrio@emory.edu).
Published Online: April 6, 2020. doi:10.1001/jama.2020.5788
Conflict of Interest Disclosures: Dr del Rio reported receiving grants from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No other disclosures were reported.
References
- Wu JT , Leung K , Bushman M , et al. Estimating clinical severity of COVID-19 from the transmission dynamicsin Wuhan, China. Nat Med. Published March 19, 2020.doi:10.1038/s41591-020-0822-7
- 2. Babiker A , Myers CW , Hill CE , Guarner J . SARS-CoV-2 testing. Am J Clin Pathol.Published March 30, 2020.
- Xie X , Zhong Z , Zhao W , Zheng C ,Wang F , Liu J . Chest CT for typical 2019-nCoVpneumonia. Radiology. Published February 12, 2020.
- Bao L , Deng W , Gao H , et al.Reinfection could not occur in SARS-CoV-2 infected rhesus macaques. bioRxiv.Preprint posted March 14, 2020. doi:10.1101/2020.03.13.990226
- Guo L , Ren L , Yang S , et al. Profiling early humoral response to diagnose novel coronavirus disease(COVID-19). Clin Infect Dis. Published March 21, 2020.doi:10.1093/cid/ciaa310
- Jefferson T , Foxlee R , Del Mar C , et al. Physical interventions to interrupt or reduce the spread ofrespiratory viruses: systematic review. BMJ.2008;336(7635):77-80. doi:10.1136/bmj.39393.510347.BE
- Bai Y , Yao L , Wei T , et al. Presumed asymptomatic carrier transmission of COVID-19. JAMA.2020. doi:10.1001/jama.2020.2565
- Bourouiba L . Turbulent gas clouds and respiratorypathogen emissions. JAMA. Published March 26, 2020.doi:10.1001/jama.2020.4756
- Kampf G , Todt D , Pfaender S , Steinmann E . Persistence of coronaviruses on inanimate surfaces and theirinactivation with biocidal agents. J Hosp Infect.2020;104(3):246-251. doi:10.1016/j.jhin.2020.01.022
- Santarpia JL , Rivera DN , Herrera V , et al. Transmission potential of SARS-CoV-2 in viral shedding observed at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Medical Center. medRxiv. Preprint postedMarch 26, 2020. doi:10.1101/2020.03.23.20039446
美国传染病专家:在新冠COVID-19疫情肆虐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些什么?
COVID-19 系列讲座
4/11/2020
Dr. Laila Woc-Colburn,MD, DTM&H, FACP, FIDSA
Director Of Medical Education
National School Of Tropical Medicine
Associate Professor- Infectious Disease
Department Of Medicine/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The video of the lecture can be watched at:
主持人:严静茵医生
整理:李芳静医生
主讲人Dr. Laila Woc-Colburn是Baylor医学院传染科主任,热带病研究室主任,chair of faculty senate of Baylor medical college, 她除了繁忙的临床工作以外,还发表了六十多篇专业文章。她在当地新冠抗疫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是参加医学院新冠领导组成员唯一的传染科医生。Baylor医学院附属教学医院每天有三十多个新冠住院病人,她是COVID-19 治疗组组长, 用了remdesivir, IL-6受体阻断剂, 血浆交换治疗。她常常受邀在当地的电台, 报纸, 市政厅发表专业意见。她最近受前德克萨斯州众议员Bento O’rourke的邀请在Instagram上发表专业意见。
下面是Dr. Woc-Colburn的讲座
A.阐述当前新冠的流行病学与预测
B.了解新冠的临床表现与预后
C.讨论新冠的治疗。
过去四个月里,我们对新冠病毒了解很多。新冠病毒是单链RNA有包膜的病毒。表面有很多棘状突起,作用于ACE2受体侵入人体细胞。肺,胃肠道,肾脏等都有这个受体。
无症状性传染
COVID 19 在华盛顿州传播。
测定了76个住在老人院的居民,23个COVID19阳性,10人有症状
13个人没有症状,其中10人随后的7天里出现症状,3人一直没有症状。
新冠的复制与反应
病毒与宿主的互相作用
1.最初是延迟或者抑制的I型IFN 反应
2.病毒复制诱发过度炎症反应。
3.激活大量的中性细胞及炎性反应细胞,如单核细胞巨噬细胞
4.诱发Th1/Th17,产生特异性的抗体。
这个过程首先发生在气管支气管,然后影响到肺泡,ACE2主要是在肺泡,临床表现以干咳为主。
新冠病毒的病情分布
80%轻症
15%重症
5%死亡
Dr.Laila分析了从NEJM来的中国的病例数据。
67例病人,
进ICU5%,上呼吸机2.3%,死亡1.4%
对老人的影响特别大
在西雅图ICU病人的病程
起始表现:
88%的病人有咳嗽与呼吸障碍,
54%的人有接触病人史
75%的病人入院时,有淋巴细胞减少
50%有发烧。
进入ICU后
75%需要用呼吸机
28%俯卧位治疗
39%全身麻醉
28%给于肺血管扩张剂治疗
0%用ECMO
结果:
最早八天拔管,
21%的人出院
29%继续住院
50%死亡。
疾病分期
Stage I 早期感染
轻度全身症状,乏力,体温超过99.6F, 干咳,腹泻,头痛
实验室检查:淋巴细胞减少,PT增加,轻度D-Dimer和LDH增高。
Stage II 肺部表现
呼吸急促,
缺氧 (PaO2/FiO2<=300mmHg
实验室检查: 异常胸部发现,低或正常procalcitonin
Stage III 炎症反应期
ARDS
SIRS/ Shock
心衰
实验室检查:炎症指标增高,如:CRP, LDH, IL-6, D-Dimer, Ferritin)
Troponin, NT-proBNP增高
新冠的临床评估
系统表现:发烧,肌肉痛。
呼吸道疾病:咳嗽,呼吸障碍等上呼吸道症状。
胃肠道:恶心,呕吐,腹泻。
五官:味觉,嗅觉障碍。
眼睛:结膜炎。
有高危的旅行史,接触史。
实验室检查:
CBC with diff, BMP,LFTs, CRP, Calcitonin
检查其他炎症指标的意义目前还不清楚。
提示新冠:中性粒细胞减少,淋巴细胞减少。
微生物检查:
-COVID19 PCR:在高度怀疑的病例,如果检查阴性,可以考虑重新检测。
-检查其他上呼吸道感染的病毒。
-考虑痰液其血液的培养。
-很重要的一点: 新冠可以与其他病毒同时感染。
影像学检查:
-所有病人做CxR
-如果诊断不明或者要除外其他病因,考虑做胸部CT。
-高度怀疑新冠: 影像学表现为Bilateral, GGO, Peripheral distribution.
死亡的危险因素
肥胖,年纪,及有其他疾病者
治疗:目前还没有可以治愈的药物。
-激素:对SARs, MERS 没有好处,在早期会延长病毒排泄。在ARDS中的使用,有争议。
-IVIG/恢复期血液:仍在试验中。
-Lopinavir-Ritonivir: 没有数据支持。
-氯喹与羟化氯喹:体外试验有效果,体内疗效不确定,可能8倍以上的剂量效果会好些。
因为80%以上的病人自己会恢复,用了这两个药以后,只是缩短一天的发烧咳嗽的时间。仍需要进一步的随机双盲研究。
-Remdesivir : 目前看来不错,等待试验结果。
-immune modulator:
Toculizumab: 有希望。
-plasma: 有希望。
疫苗
各个国家都在研发中。
问题解答:
1.关于隔离时间
如果接触了新冠阳性病人,可以回去上班,但需要带外科口罩。
如果有症状,应该等14天或者发烧恢复以后7天。
有时候症状恢复以后21到28天,还是可以有病毒排出,PCR阳性并不能告诉我们是不是有传染性,所以我们需要测定血液中IgG
2.羟化氯喹是不是应该给老人和体弱的人用?
这个药的使用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
如果医生务工作者有接触史,可以考虑预防用药,400mg 第一天一天一次,然后200mg a一天一次四天。
3.在long term care中Protocols .
Dr.Laila advised to google:
UW coronavirus protocol
4.PPE使用的policy
在COVID unit,ER:
应该带护目镜,N95口罩,头发也可以包起来,最好是用像中国医生那样的防护服。
5.COVID 轻中重度怎么分类?
轻度:在普通的空气里,病人没有缺氧现象,尽管有咳嗽,发烧等症状。
中度:需要用氧气。1-2L,血氧饱和度在94%以上,感觉还可以。
重度:就是到了ARDS,插管的情况。
6.羟化氯喹的副作用是什么?
-QT延长
-在有精神疾病的病人中,有出现失眠癞痫的副作用。
-在慢性肾病的病人中,有出现Tonic- clonic的付作用。
-当然,大剂量可以有眼睛的毒性。
-在有G-6PD缺陷的病人,会引起溶血贫血
Dr. Laila 觉得,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羟化氧喹的使用。做为医生,first is to do no harm.
因为80%的轻症病人不用羟化氯喹就会恢复;用的话,只不过缩短一天的发烧咳嗽时间。
7.对早期美国口罩使用的看法。
在美国可能早期使用口罩会有帮助,但是这里有多种文化及习惯。对有的文化来说,带口罩是一个污点。
8.出院病人回家以后的隔离
根据每个家庭的情况而定,建议继续隔离14天。
幻灯片见下:
张文宏: 上海防控与救治COVID-19经验分享
上海防控与救治COVID-19经验分享
3/28/2020 ANACP 讲座记录
主讲人 张文宏教授
主持人 李芳静医生
李芳静医生整理
大家好,很高兴能为大家主持今天的讲座。
首先, 感谢刘健医生,为我们联系到了百忙之中的校友,张文宏教授。
张教授是上海市anti-COVID-19临床救治专家组的组长,复旦大学 华山医院 感染科主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内科学 系主任,有着丰富的anti-COVID-19临床经验。
以下是张教授的讲座的内容
张教授昨天还在和欧洲的专家们视频讨论,目前的重灾区在欧洲。估计美国的高峰在四月中上旬,要在夏天结束很困难。
美国第一波防疫控制不错,但是留下了后门,就是没有控制与欧洲,澳大利亚等地区的联系。
美国第二波的控制,阻断社区的传播没有成功。
中国第二波的控制很成功,现在都是输入型的感染,没有当地社区的传播。
上海一月底的病例主要是从武汉来的,按照当时流行病传播的模式,推算到上海会有80万人受感染。在严格控制后,最后只有350人发病。
在武汉是采取了彻底lock down的对策,对控制疫情扩散,有很大的帮助。
而上海并沒有完全shut down,张教授领导的专家组一直在宣传,让大家Stay at home, 大家都很自觉。尽管大的商场,食品店都是开的,但去的人很少。关闭了地铁与公交汽车,政府也将春节结束时间从1月24号延后到2月9号。
在上海,如果有疑似病例就收入隔离病房;如果PCR检测阳性,就收入新冠治疗中心,由张教授领队的专家组专门治疗。
张教授曾几次与美国的专家讨论,在国内大部分病例,都能追踪到传染源,并隔离接触者;在美国,只能追踪到一部分。
现在纽约及其他部分城市采取curfew 宵禁措施,关闭餐馆,大型商场,娱乐场所等,应该会有所帮助。两周以后,如果新病例不再增加,那么形势会慢慢好转,如果新病例还在增加的话,形势会变得非常严峻。
张教授主张要多做检测,标准是有发烧及有接触史的人都需要检测,这样能做到及时隔离,防止传播。CT 上的小病灶异常,有时候很难区分是轻症新冠肺炎还是与其他病原体引起的肺炎。
一般病人症状出现的中位时间,是在6-7天左右。比较严重的,从出现症状,到需要住院治疗,是四到五天。
关于治疗问题
现在上海新冠治疗中心的161例新冠患者,目前还没有一例需要气管插管。最好是能够不用invasive mechanical ventilator。
现在的意大利、西班牙以及中国早期的武汉,病死率高,是因为病人太多,呼吸机严重短缺,病人一旦出现缺氧,就没有办法控制。也非常缺ECMO。
美国是全世界呼吸机及ICU最多的国家。
美国如果两周以后新发病例不再增加的话,目前的医疗资源应该可以应付。不然的话也会出现短缺。
华盛顿州的大暴发与养老院大批老人受感染有关。
药物治疗方面。
张教授本人没有试用过Remdesivir 。
但他用了所有其他的抗病毒治疗的药物,以及羟化氯喹,目前还没有获得非常肯定的效果,要等最后的研究结果出来。
法国医疗团队关于羟化氯喹与阿奇霉素疗效的报导,设计有些问题。张教授他们在新冠病人的治疗中,没有办法得到类似的临床效果。
羟化氯喹副作用不大,在疗效上还不能属于“神药”一类。
上海关于羟化氯喹的随机试验结果,最近会发表出来。
病死率与医疗资源的充足程度肯定有关。
法国的病死率是7%。
德国的病死率是0.5%,他们的医疗资源很充足。
上海的病死率1%左右。上海最近17例新冠并发ARDS,都用上了呼吸机治疗。
抗凝治疗在新冠的治疗中非常重要。住院病人需要监测D-Dimer, FDP, LDH。
LDH 增高与死亡率有关。LDH大于500时,死亡的可能大大增加。
早期要非常积极的对症治疗。
1.支持全身器官的正常功能。
2.稳定各项生命指征。
3.足够的营养补给。
4.镇痛治疗,如果需要的话。
5.控制好氧饱和度,用nasal cannula, ventilators, ECMO等。
严重新冠病人肺纤维化的情况,不是很常见。
关于激素的使用问题。
皮质类固醇的使用需要很谨慎,大部分时间不需要用。
只用于少部分病人,有缺氧情况但不是很严重,肺部影像学病变发展很快,可以用一周左右,剂量在0.5-1mg/Kg
气管插管以后一般就不要用激素了。
然后张教授回答了一部分医生朋友的问题。
1,从感染科医生的角度,中国全民戴口罩对于对抗COVID-19是否有效和必要?如果必要,您预计国内民众口罩还要戴多久?
是否应该戴口罩,取决于当地的情况。
如果发现病人数多的情况,带口罩会有帮助。
听说德国也在改变,准备让大家戴口罩。
但是全民戴口罩,需要有充足的口罩来源。
2,支援武汉的医务人员都没得新冠,是不是完全归功于PPE的正确使用。
是的,高规格的PPE很重要。
现在国内医护人员的PPE比美国的要好。
3. 如何预防炎症风暴?出现这个反应早期临床表现是什么?有了以后主要用什么药?
如果CT 进展很快肯定要查D-Dimer, LDH, CRP, Cytokines 如IL-6。
尤其是LDH增高,大于500的话,预后很差,没有很好的干预办法。
抗凝很重要,支持疗法,激素使用(见前面)
IV Vit C在septic shock病人可以用到的一天5-10Gram。可以用于重症COVID-19的救治。
4. 有一部分20-40岁,从轻症变成重症的病人,患者有什么相似的risk factors吗?年轻轻症患者目前大多数在家里隔离观察,有些什么征兆or signs需要大家注意的吗?
如果病人有其他疾病如心肺病疾病,及缺氧等情况,要引起警惕。
5. 如果目前大量无症状携带者不收治、会不会成为潜在因素引发第二波爆发?
主要是发现及隔离。
少数无症状带病毒者,病毒量(viral load)最高是在七天左右,二周后基本测不到了。
6. 病人症状没有了之后还要继续隔离多长时间,看报道有测试结果阴性出院又转阳,是本身病情反复还是又被感染?
这种情况一般是出院的时候没有测到病毒量,可能那时病毒量很少,回家以后活动增加,痰液可能被咳出来,一些残留的病毒核酸可能可以检测到,并不是又被感染。
7. 病毒在空气中存活多久?密切接触才传染,请具体”密切接触“方式。
据目前所知新冠病毒可能有气溶胶的现象存在。
一般家庭成员的互动,都是属于密切接触。
8.儿科病例的诊断, 治疗及发病率和治愈率.
儿童患者较少,而且症状都比较轻。
9.医务人员接触新冠病人后,一般几天后测定会阳性.
医务工作者接触病人以后,不管结果如何,都要隔离7-14天,取消隔离时候要做测试,。
10.新冠胃肠道表现除腹泻之外,对胃肠功能有什么其他影响,作用机制是什么?
这个病毒除肺脏外,还作用于肠道的ACE2受体感染肠道,可以有腹泻便秘及各种症状。
11.听说国内口腔医生复工穿防护服,能谈谈口腔科医生在诊治病人时应该注意的防护吗?
在新冠爆发的时候,牙医诊所都关门了,所以有牙痛的病人很痛苦。
牙科医生应该穿戴所有的PPE,护目镜,N95,gown
12.有没有牙医被感染的数据?如有,是与工作有关还是社区传播?
根据目前的资料,主要是社区感染的。
13.听说国内有人用Entecavir 来prophylaxis?
这个药没有用,所有抗病毒的药物都有待于临床研究确认。
14.检测临床隐性感染新冠病毒的人群,血清抗体治疗效果?
有的抗体没有中和作用。
15.重复感染的几率是多少?有症状者检验阳性转阴性以后再复发阳性的几率是多少?
张教授也与美国的专家讨论了这个问题,目前的观点是,感染了新冠病毒以后产生的抗体有防止再感染作用。
16.普查抗体指导早期复工的可行性?如果只查IgM,怎么判断无症状者是处于潜伏期还是恢复期?
只用Ig M很难判断。最好还是同时做核酸检测。
感谢张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座。对我们目前的抗疫工作很有帮助。再次感谢你 张教授,在繁忙的工作中抽时间与我们交流。欢迎你有机会来美东玩。
北美华人医生联盟(ANACP)是非营利组织,自2016年成立以来,致力于会员之间的交流与对社区的医疗服务。今年年会定于11月在亚特兰大城举行,希望在大家的努力下,疫情得到完全控制,大家能够相聚在五彩缤纷的秋色里。
谢谢大家,谢谢杨文医生,程淮勇医生,汪策医生及其他医生会员无私的奉献和付出。
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纽约,与死神博弈: 华人一线医生淡定从容?
我们医院的情况也好不到那里去,整个医院都变成了covid land。我们医院的PPE和isolation gowns全面告急,ICU已经基本弹尽粮绝。周五医院command center 紧急开会商讨对策。有人提出去Costco 买垃圾袋缝制 isolation gowns——” Better than nothing ”。我的同事Dr. C 偷偷告诉我,“Wen, They are going to use rain ponchos and garbage bags, like mount Sinai。“ 我们麻醉科因为有华人社团和朋友的捐助,所以目前还有足够的PPE(图一,二)。
图一,我和同事穿着上海的朋友给的防护服去ED插管
图三 ,我蚂蚁搬家似的往医院运PPE
不一会儿就收到了同事的message 。“We should do something for Wen when this is all over. She has saved us for all these PPE donations”; “Yes. I agree . M and me will treat you . We appreciate you Corona Santa. And when it’s all over , we have to send thank you cards and gifts to Each of your friends” ; “From department I will collect if I haven’t died ”。
这天我值OR的班,接班不久就接到了covid 19 intubation , 我跟Dr.C 穿上我们的bunny suits 就冲到病房。病人是一个五十几岁homeless的黑人。Dr. C 打开病人口腔,里面全是痰痂。小屏幕的McGrath可视喉镜上根本看不到啥解剖结构,我们不得不快速吸痰。换了一个大屏幕的glidescope (图四), second attempt才把管插进去。
图四,我们科临时的covid 19 intubation station
我们俩刚回到办公室,第二个code blue 就到了。这次看上去是个和蔼的印度裔老太太;呼吸40多次,戴着non-rebreather Mask,氧饱和度只有70%。见鬼,推完肌松药老太太两只眼睛还是直勾勾盯着我。“shit, IV infiltrated” 。Pulmonary fellow 马上 place central line 。十分钟以后central line 顺利完成,我的goggle 也被汗水搞得一片模糊。我顾不上暴露不暴露就把goggle 往脑门上一推,先把管插了进去再说。
回到办公室,在ICU忙了一天的麻醉护士S 声泪俱下得告诉我们,她管的病人-我们的medical student V的妈妈刚才走了。V的妈妈只有54岁,住进SICU还不到两天。虽然入院后马上气管插管并上了呼吸机,但病情还是急转直下。因为V是我们的学生,医院破例允许他探视。V一直陪在妈妈的身边,揉着妈妈的腿sobbing 。因为是传染病,死于新冠的病人都不会有funeral。Body 被拉走之前得把身上所有首饰都取下来,V一边哭一边帮妈妈取下手上的戒指。麻醉护士S觉得这孩子太可怜了,就对他说“you want a hug ... oh , no , I can not hug you ... I may have virus already ...do you need help ?“ , V 黯然得说 “ I guess I have to tell my father and sister.” actually, His father was sick too.
还有一家三口,全都因covid 19重症,住进了我们医院。不幸的是最年轻的儿子,已经先走一步。剩下的老两口连白发人送黑发人最后一程的机会都没有,他们各自在不同隔离病房里忍受病痛和丧子之痛。医院想破例让老两口Co-house 。这样无论将来发生什么,至少老两口还可以看到对方。
不过,在阴霾密布的日子里,有时候我们也会有好消息。这不今天同事C就高兴得告诉我,我们上个周一做的剖腹产, BMI 55 , covid 19 的病人顺利拔管脱离了呼吸机。虽然妈妈covid 19 阳性,baby boy covid 19 还是阴性。我们终于可以对病人说母子平安了。是的,看到了希望,我们就有了坚持下去的理由。
突然和完全的嗅觉丧失功能可能是COVID-19的症状
由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冠状病毒-2(SARS-CoV-2)引起的新型冠状病毒病-2019(COVD-19)偏爱感染人类呼吸道上皮细胞。SARS-CoV-2感染患者的临床表现为包括下呼吸道感染伴发烧,干咳和呼吸困难。相比之下,上呼吸道症状较少见,表明该病毒攻击的靶向细胞可能位于下呼吸道。
迈克尔·埃利泽在“JAMA耳鼻喉头颈外科手术”报道了一例SARS-CoV-2感染患者表现出的主要症状是:嗅觉功能突然,并完全丧失而无鼻塞的症状。
这是一名40多岁的妇女,表现出嗅觉功能严重丧失而无鼻塞表现。但她没有味觉异常,没有失去咸,甜,酸和苦的鉴别。在嗅觉丧失前几天,她还出现了干咳,头痛和肌痛。她没有发烧或流鼻涕。耳镜和前鼻镜检查结果(未经内镜检查)均正常。
使用5种测试人的嗅觉的气味来评估检测和识别气味的能力:苯乙基酒精(花玫瑰),环戊烯(焦糖),异戊酸(山羊乳),十一内酯(水果)和粪臭素(粪肥) )。目的是检测患者可否识别每种气味。结果发现这些气味患者都未能识别到。
患者鼻腔计算机断层扫描(图1)显示了鼻腔的双侧炎症性阻塞。嗅裂的双侧阻塞(黄色箭头),其余的鼻腔中没有阻塞现象。
上述CT变化在鼻腔的磁共振成像(MRI)上得到了证实(图2)。嗅裂和嗅球的冠状切面(A)二维T2加权序列和(B)三维T2加权序列; 嗅球(蓝色箭头)是正常的,而观察到嗅裂的双侧炎性阻塞(黄色箭头)。右上颌腔粘膜轻度增生。
病人嗅球和嗅道没有异常。
由于她的丈夫已被怀疑感染了SARS-CoV-2,因此对患者做了SARS-CoV-2实时聚合酶链反应(RT-PCR),结果呈阳性。
上呼吸道感染是嗅觉丧失的最常见原因之一,占病例的22%至36%。这名COVID-19患者影像学表现为双侧阻塞性嗅裂炎症,通过阻止气味分子到达嗅觉上皮,严重破坏了嗅觉功能。
这种阻塞的起源仍然未知,以前在严重的鼻咽感染后的患者中已有报道。但是,在该患者中未发现鼻腔阻塞或流鼻涕。
大多数冠状病毒具有相似的结构和感染途径。因此,可以预期SARS-CoV-2的相似感染机制可能是通过靠近嗅球和嗅上皮的筛状板侵入大脑。
最近,Ligget等[描述了嗅觉受体家族在中央皮层神经元,血管平滑肌以及上,下气道上皮细胞中的表达。由于SARS-CoV-2通过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受体的损伤感染人类呼吸道上皮细胞,因此作者认为该嗅觉受体家族也可能受到选择性地损伤。
这是首次COVID-19病人表现为嗅觉功能丧失的报告。正如法国耳鼻喉学会(https://www.snorl.org/category-acces-libre/alerte-anosmie-covid-19-20-mars-2020/)报道的那样,作者认为如果病人具有其他Covid-19症状(例如咳嗽或发烧),又有突然,完全的嗅觉功能丧失,但没有鼻腔阻塞,临床医生应该怀疑有SARS-CoV-2感染。
Ref:
Sudden and Complete Olfactory Loss Function as a Possible Symptom of COVID-19
Michael Eliezer, MD1; Charlotte Hautefort, MD2; Anne-Laure Hamel, MD2; et al
Benjamin Verillaud, MD2; Philippe Herman, MD, PhD2; Emmanuel Houdart, MD, PhD1; Corinne Eloit, MD2
Author Affiliations Article Information
JAMA Otolaryngol Head Neck Surg. Published online April 8, 2020. doi:10.1001/jamaoto.2020.0832
Corresponding Author: Michael Eliezer, MD, Neuroradiology Unit, Lariboisière University Hospital, 75010 Paris, France (michael.eliezer@aphp.fr).
Published Online: April 8, 2020. doi:10.1001/jamaoto.2020.0832
Conflict of Interest Disclosures: None reported.
Additional Contributions: We thank the patient for granting permission to publish this information.
“羟氯喹+阿奇霉素“联用: 警惕严重的心脏副作用
最近有关羟氯喹抗新冠的话题很引人关注。有报道“羟氯喹+阿奇霉素”联用可能有更好的效果。可是,羟氯喹或者阿奇霉素这两药都分别可能导致严重的心律失常,即“QT间期延长”。当这两药合用时这副作用将可能更严重,即可产生“心电图QT间期”延长的机会更多了,甚至可导致“尖端扭转型心律失常”,后者或可致“猝死”,非常危险。为了让人们对这两种药及其副作用有清晰的认识,以免被误导,那么针对下面几个问题:1.对于“羟氯喹”和“阿奇霉素”这两种药在实际临床中应在什么情况下使用?2.联用的适应症是什么?3.该怎么联用,联用时要注意什么?4. 患者可以自己在网络上购药自己治疗吗?这篇文章我们就上述这些问题进行阐述,以警读者。
一、“羟氯喹”和“阿奇霉素”分别是什么药?
羟氯喹,是一种老药,在美国从1955年以来就已经长期在临床上使用。它主要用来治疗疟疾、红斑狼疮和类风湿关节炎等疾病。羟氯喹的主要严重副作用包括心肌损害和心律失常,后者包括心电图QT间期延长。对于有“先天性长QT综合征”、“QT延长家族史”,“QT延长”,“电解质异常”,“室性心律失常”、“尖端扭转型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患者应禁用、或者非常慎重使用。一般的健康的人,即使没有上述心脏病或者相关病史,医生会建议在用药前,用药后均应定期查心电图,还包括查钠、钾、镁等血电解质。
阿奇霉素, 是一种常用的抗生素,在美国发行每年超过五千万的处方。一般用于治疗呼吸道感染、肺部感染、泌尿系感染。此外阿奇霉素对支原体肺炎的治疗也有很好的疗效。近几年,医学界对阿奇霉素副的作用已经很警惕。2012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一项研究显示: 相对于阿莫西林, 使用阿奇霉素导致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增加2.49倍。在2013年也是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有评论文章警告:药理学和流行病学数据都显示使用阿奇霉素等抗生素有潜在的导致QT间隔延长这一致命心律失常的潜在后果, 医生在开处方决策中应充分考虑到这一风险,衡量用该药进行抗菌治疗的风险和收益,特别是对于预先存在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更应该非常谨慎。给有先前存在的QT延长疾病, 或包括低血钾,低镁血症和使用其他延长QT的药物,危险因素的患者开阿奇霉素处方时应格外小心。
二、“羟氯喹” “阿奇霉素” 可能的抗病毒机制在哪里?
根据体㚈试验,氯喹可能是通过抑制病毒ACE2的糖基化或者抑制了醌还原酶2,减少了病毒唾液酸的合成,从而杀死病毒。阿奇霉素在这一联用方案中可能有抗炎症,协同和增强抗病毒作用,但具体机制目前还不清楚。
三、“羟氯喹+阿奇霉素”治新冠的适应症是什么?
“羟氯喹+阿奇霉素”治新冠可能效果更好仅是基于“传闻性”“极小样本”的资料(Anecdotalevidence),目前还没有经“大样本的严格的随机双盲”科学临床试验。然而,由于目前全球新冠疫情严峻,基于“同情治疗”的医学伦理角度出发,羟氯喹,或者“羟氯喹+阿奇霉素”目前是美国等多个国家治疗住院的中、重度,或者是“疾病进展期”的新冠患者可选择的方案之一。据说,羟氯喹,或者“羟氯喹+阿奇霉素”联用可以减缓病情向重症转化。
四. 为什么一定不要在没有心电监护的情况下联用“羟氯喹+阿奇霉素”
心电图中的QT间期是从QRS开始到T波的末端。通常,正常QT间期小于400到440毫秒(ms),或者0.4到0.44 秒。女性的QT间期时间可能比男性更长。由于心律的影响,经常使用校正后的QT间期 (QTc)。由于心率的影响,经常使用“校正的QT间期”。
如果男性大于450 ms,女性大于470 ms,则认为QTc延长。对于将羟基氯喹和氯喹用于COVID-19感染患者的患者,考虑以下可修改选项:
•带有QTc评估的ECG
•避免不必要的延长QT的药物
•识别和纠正电解质失衡(钾,镁,钙)
•停止使用不必要的延长QTc的药物
•考虑可能会增加羟基氯喹和氯喹治疗水平的合并症,例如急性肾损伤或肝病。
基于上述信息,由于羟氯喹和阿奇霉素这两种药物都延长QTc,这两种药在分别单独使用的时候己经都需要这么慎重了,当把它们联合应用时,其危险性可想而知。虽然这副作用非常罕见,但是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所以,我们建议这两药联用时,一定不要在没有心电监护和电解质监护的情况下联用。
除了氯喹,羟氯喹和阿奇霉素可导致QTc延长外,最近应用在COVID-19 治疗的HIV药洛匹那韦和利托那韦 (克力芝) 也可能有诱发的室性心律失常和心源性猝死的风险。在开始使用这些药物治疗之前,重要的是要做一个基线心电图。这个基线测量可以来自标准的12导联心电图、遥测或智能手机支持的移动心电图设备。3月20日 (星期一),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了AliveCor的Kardia 6L移动心电图仪作为FDA批准的唯一一种COVID-19监测QTc的移动设备。移动设备能够远程提供患者的心律和QTc,不需要额外的ECG技术人员亲自进行测量,从而节省了对COVID-19的更多接触和对更多个人防护设备的需求。
五.患者可以自己在购药自己治疗吗?
在美国,这两种药都是处方药,必须有医生的处方才能买到药。然而,某些人可能通过不同渠道获得这些药。患者不在医生指导下自己购药自己治疗对任何药都是很危险的。对于自己购买和服用羟氯喹,或者“羟氯喹+阿奇霉素”其危险性实在太大,绝对不可以这样做。总之,“羟氯喹+阿奇”联用目前仅是基于“同情治疗”在医院内,用于中、重度新冠肺炎。因为存在的包括可能致死性罕见副作用,当把它们联合应用时,其危险性更大, 我们建议须在医生指导下,在各种监护包括心电图和电解质监护下非常慎重地使用。最近听说有一位患者自己购买和服用氯喹后死亡,妻子病危。因此,对于“羟氯喹”或者“羟氯喹+阿奇霉素”绝对不可以“自己做医生”自购自服。
主要参考文献:
1. Colson P, Rolain JM, Lagier JC, Brouqui P, Raoult D. Chloroquine andhydroxychloroquine as available weapons to fight COVID-19. Int J AntimicrobAgents. 2020 Mar 4:105932. doi: 10.1016/j.ijantimicag.2020.105932. [Epub aheadof print]
2. cdc.org
3. COVID-19 HydroxychloroquineTreatment Brings Prolonged QT Arrhythmia Issues, March 24, 2020| Marianne Pop,Pharm.D, BCPS.
4.Al-Khatib, et al., What CliniciansShould Know About the QT Interval . JAMA. 2003;289(16):2120-2127. doi:10.1001/jama.289.16.2120
5. Mosholder AD et al., Cardiovascular Risks with Azithromycin and Other AntibacterialDrugs, N Engl J Med 2013; 368:1665-1668
作者:
林艳丰 美国宾州医院医学/家庭全科
郑景生美国新泽西州心血管专科
一个Primary Care Physician是怎么样应对COVID-19 的?
武汉,湖北,中国的抗“疫”COVID-19是海外华人,尤其是在海外行医的华人的上半场。美国的疫情一开始,我们美国华人的下半场就开始了,连中场休息的机会都没有。昨天, 3月26日,美国的COVID-9 病人总数(83,509人)超过了中国。今天在校友群看到一对在海外行医的夫妇和6岁的孩子都中招了,而且丈夫已经气管插管,进ICU抢救。看来我们必须准备打加时了。我从美国发生第一例社区流行以来,针对我的病人特点和我私营诊所的特点,同时考虑到我有可能被感染而传给我丈夫的可能性,进行了如何打好下半场的一些准备。 我行医20年的诊所在宾夕法尼亚州府哈里斯堡。哈里斯堡是一个中等大小的城市,城市和郊区总人数大约20万,分得很散。我们诊所大约有5000病人。我们一共有3个MA(Medical Assistant),一个 Nurse Practitioner, 和 2 个儿科医生(equal partner)。自从第一例美国社区流行起,我开始准备四个本地社区流行时的运作总方针:(1)尽量减低我们诊所医护人员被感染;(2)保证病人得到及时的医疗服务,尤其是与COVID-19无关的医疗服务;(3)保证MA和Nurse Practitioner 有与流行前等同的工资;(4)尽量减少我丈夫被我感染的可能性。在这些总方针的框架下,我开始着手具体操作.
在武汉还没封城时,我购置了两盒N95 的医用口罩和100个外科口罩。当时想,反正平时看流感,我也要用的。后来,想通过我平时的供应商为海外校友会区购买N95口罩之事未果,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立马开始节约使用有限的资源。二月二十六日,又通过大学同班同学购买了一些N99的口罩。我们这个地区,是3月11日首次报道3例COVID-19,而且都有意大利近期旅游史。我第二天就开始要求诊所所有员工戴口罩接诊所以病人。开始时,这个戴口罩上班的要求,非常“不得人心”。所以人人都反对。我反复跟大家说,这是对我们自己负责,也是对病人负责。但是仍然很难被接受。我的Partner 特别不接受这种“可笑”的工作方式。两天后,一个去年在我们诊所工作的MA的经历,改变了所以人的行为。这个MA在Urgent Care 第一个接诊一名病人,urgent care 顾名思义,是紧急看病的地方。不需要预约,直接去就可以了。这个病人和MA都没有戴口罩。一直到病人跟医生打交道时,医生才意识到这是一个(patient under investigation, PUI)的患者。最后该PUI 确诊, 是本地的首例COVID-19。 这个MA立马居家隔离。三天后有症状去医院检测COVID-19,她是单亲母亲,有两个7岁和2岁的孩子。我就用这个事儿去说服我们诊所的全体医护人员,上班全体戴口罩接诊病人。这次“苦口婆心”终于让大家意识到了口罩的重要性。
三月六日,我先生在Amazon 买了一只36W的紫外线灯管。十五日,星期天,在诊所安装成一个可以移动的紫外线消毒灯。我还在先生的帮助下把一个诊室改成专门诊治感染性疾病的诊室。改装的主要目的是把空调系统的出风口和空气循环入口密封起来。主要是防止病毒通过气溶胶转移到其它诊室和医生办公室。这个诊室每看完一个病人,就紫外线消毒一次。我同时决定,把这间诊室用来做紫外线消毒工作服和口罩的房间。在墙上订了好几个挂衣服和口罩的挂钩。
除了口罩以外,我们没有防护服,也没有护目镜。我把20多年前做住院医时的用的 “工作服”(scrubs)找出来,带去分给大家上班时穿在最外面。每天中午和下班时紫外线消毒。
2. 保证病人得到及时的医疗服务,尤其是与COVID-9无关的医疗服务
我觉得这次COVID -19 的社区大流行,不是关门停业就能解决的。美国的大多数病人的医疗保健,是靠各种大小不等的私人机构来提供的。如果我们这样的诊所都关门在家,我们的病人将会恐慌而去挤压附近的医院的急诊科。而且,这些病人的与COVID-19没有半点关系的医疗服务将没法进行。针对这个情况,我们3月17日开始经行严格的分诊程序。也同时开通了Tele-Medicine 的诊治模式。我们的分流程序可见图片。
我诊所的共识是,首要任务是尽最大努力,保护医护人员不被感染。因为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的病人将会参与挤垮美国的医疗体系立的大潮。其结果将会导致非COVID-19 的死亡人数会远远超出COVID-19 的死亡人数。
在上面两个措施的基础上,我们诊所目前的运行理念是:
1,医护人员开始使用口罩。因为资源不足,应该节约,很多情况下,可以消毒后再用。目前我们N95口罩每四个小时(中午吃饭时)换下来,消毒后留给第二天早上用。下午开工时,使用当天的第二个口罩。下午下班时进行消毒,第二天下午再用。这样,每个工作人员,用两个口罩轮回周转。每个口罩我们目前用6次。
2,与COVID-19可能有关的病人,按上图的分诊流程,轻症在家呆着,医生通过电话,短信,email 指导支持疗法。症状较重的,送去我们医院的ER特设的COVID-19 专用场所进行病原学检测。如果排除了,再跟医生办公室联系,通过Tele-Medicine给与相应的治疗。
3,严格限制陪诊人数,只让一位家长陪同进诊所。早到的病人,在车里等候。没有邀请,先别进门。
4,能通过E-medicine 的,一定要走这条路。
点赞一下,川普总统宣布national emergency declaration 时,发布了开展E-medicine, 而且,CMS 开始reimbursement e-medicine,各个保险公司都开始接受E-medicine。这个非常重要。这样医生就可以收到合理的professional charge。有了收入,就可以发工资给自己和员工。
这是2020/3/24 CDC 检测COVID-19 的三级优先检测指南:
3. 保证MA和Nurse Practitioner 有工资
随着COVID-9 的快速传播,病人的每日就诊人数比过去少了很多。我们的进账已经减少了很多。考虑我们的MA和nurse practitioner 都是靠每次的工资维持生活的,是live pay check by pay check 的典型美国中产阶层,我们已近开始实行每天一个provider 在办公室上班。The Nurse Practitioner每周上两天班,两个老板,每周上1.5 天的班。MA 天天上班。我们还取消了星期六的门诊,改为E-medicine。我们三个provider基本上不在诊所同时出现,减少3人都同时需隔离的可能性。我非常希望我们能维持下去,一直到疫情结束。我觉得这点“牺牲”应该是我们一起来保卫我们的家国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实事。这样一来,其它员工拿跟过去相同的收入,而我们两个老板的收入立马下降了63%。感恩美国给了我行医的机会和我先生可以完全在家工作的优良待遇,我非常赞同一位为ECMO有非凡贡献的的校友说的“美国给了我们非常好的经济回报,我们一定要把这里真正的当成自己的家自己的国来保护”的肺腑之言。
4. 尽量减少我丈夫被我感染的可能性
我现在上班穿scrubs, 每天消毒两次,下班前衣服,裤子,鞋子全部紫外线消毒。上车前鞋底喷Lysol。回到家,衣服脱在车库里,到楼下卫生间洗头,洗澡。我和很多在美国行医的同行一样,家里有不是医生的丈夫,有不是医生的儿女(她在NYC,是现在的最危险的地方)。他们都需要我的关爱和具体“抗疫建议”。除了NPI(Non-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外,我是这样分别对待的:
先生:他和我同住一个屋檐下。我们三月二十一号开始,就睡在不同的房间,用不同的卫生间了。我们吃饭的时候,也保持一定的距离。 他必须出去购物和加油时,保持与他人2米的距离,随身携带酒精消毒液。尽量保持一个手是不被污染的,另一个手用来做所有的接触东西的事。上车前先消毒手,再开车门。购回的物品,先放好,过24-48小时后,再使用。拿回来的信件,放24-48小时后再打开。
女儿:不是万不得已,不出门。必须出去购物和加油时,戴好口罩。其它注意事项,与先生大同小异。脱下的口罩可以放在一个纸袋里重复使用。这个戴口罩的建议,我认为目前是有助于减低被感染的危险性的,尤其是在人口密度较大的地方。
我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努力,为美国抗COVID-19贡献一点点微博的力量。也希望我的这些措施,能给读者提供一些比较实用的防疫措施。
何明花医生的简历:
湖北武汉市人。1978年考入武汉医学院。
1983年武汉同济医学院临床儿科专业毕业。
1983-1990 在上海铁道医学院上海铁道局中心医院(现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甘泉医院)当儿科医生。
1990-1997在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北卡大学)从事神经学研究。
1997-2000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医学院儿童医院完成美国住院医师培训。获美国儿科协会认证(FAAP)。
2000-今 Harrisburg Private Practice 工作至今。
美国抗新冠战疫的防御战:抗新冠时期随笔(4)
今天是3月29日,周日。成年后,时间从来就是一种奢侈品,时光如白驹过隙,日子从来都沒有感觉过得像今年这么慢过。历史上,只有老板付钱让员工上班的,从来沒见过象现在这样老板付钱求员工待在家里的。对于单身收入七万五千美元以下的,会收到联邦$1,200的支票,家庭两口总收入十五万刀以下会收到2,400刀。
自从新冠于1月20日在美国西雅图确诊后,二月二十九日华盛顿州老人院出现因新冠而死亡的第一例,今天整整是一个月,一个月前确诊病例为79例,而在写此文时,已经是141,239例确诊,2,487例死亡了,不过目前病死率还是算低的,1.7%。
抗新冠就如同一场惨烈的战疫,敌人是Covid-19, 目前敌人力量还在处于上升阶段,估计还要等两周到复活节,有可能转到相持阶段,即峰值。几个模型都认为,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美国可能会有一百六十万至二百二十万人死亡,如釆取措施,可能仍有8到10万人死亡,这大大超过了我以前的想象,看来这新冠病毒果然来势凶猛,狡猾难缠。全球几乎所有国家地区均被攻破,全美50州无一幸免。美国确诊人数一夜暴富,成为全球之冠。当然美国核酸检测数量亦为全球之首,迄今,已测了八十九万四千份了,马上会测的更多,确诊数会迅速地增加。所以今天总统宣布把“社交距离”这一方法延后至四月三十号。这样,自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不能聚在一起公开庆祝耶稣复活节了。
不管对美国总统有什么评价,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工作勤奋,每天除五个小时睡眠外,几乎每天都是开会、电话,每天亲自召开白宫新闻发布会,透明度是可以的了。
纽约是美国新冠发病中心,纽约的走向是美国新冠走向的风向标。纽约州长库欧默,也是每天上午开新闻发布会。联邦政府为纽约抗疫输送了很多子弹,这点州长也承认,然而一线却不能感到这一点,据说很多子弹还存在弹药库里,看来有人在囤货,还有两位护士助理感染而牺牲,川总对此很不爽。
今天在记者招待会上,总统与记者斗争之后,居然看到了老川男儿柔情的一面,他告诉大家,他在纽约昆士出生长大,那儿的Εlmhurst医院他熟悉的连哪面墙是什么颜色,哪面窗户是什么样子都历历在目。昨晚上看电视,他见到医院外卡车运送尸体,他不可思议发生在家乡,这居然是美国,说着说着,差一点儿就没控制住自己而落泪。不过这可是美国总统在全世界面前黑美国啊,这是自信还是透明?
好了,在战斗相持阶段前,黎明之前黑暗中也看到了一丝丝曙光。纽约每日新增病例也已持平。
诊断方面,Abbott公司推出了五分钟即出结果的检测仪,据说是俺州一位华人领导的团队一周日夜奋战搞定的。此外,病人自己取样自己检测试剂盒也到位了。Humana 及 Cigna 两个医疗保险公司将免去与新冠相关疾病的任何Co-pay。
治疗方面,FDA批准了同情用药:羟氯喹,阿奇霉素联合用药,恢复期血浆,Remdesivir。疫苗仍在病人临床试验中。
纽约Javits会议中心在美军工程兵快速建设下,不到四天,建成了有二千九百个床位的移动医院,美国的“方舱或雷神山”?不过这不是用于新冠病人的,而是用于非新冠病人。
美国海军医院船舒适号(Comfort) 昨天下午在总统目送下,离开了弗吉尼亚州,周一将抵达纽约港,本船有一千张床位,八十张重症监护室,12间手术室,船上没有攻击性武器,只有自卫武器,战争中若对该船的任何攻击,便构成犯罪行为。本船亦不作新冠病房用,而是用于非新冠病人。
供应链方面,自总统签署了参众两院通过的2.2兆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后,物资采购立即顺利起来。总统上午在白宫召开了供应链会议,包括FedEx, UPS, Cardinal Health, Henry Shein, McKesson, Owen & Minor, Medline等公司均参与各种供应链管理,保证物资供应充足,其中还有启动消毒口罩方法。会有几十架飞机从亚洲运物资来美国,今天第一架已从上海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飞机上装有80吨PPE, 其中含一百三十万个N95口罩等,还有各种防护品(1200万只手套,170万只医用口罩, 50000套防护服,130000瓶洗手液,36000只体温计),美国其他公司也在生产这些防护品。GM准备生产呼吸机。连电视上卖枕头的Michael Lindel也开始生产口罩了,看来,战斗号角吹响了,美国国家机器启动了,相持阶段就会到了,复活节希望见“拐点”,希望六月见分晓。
芝加哥方面出现了第一例二岁以下儿童死于新冠病例。
校友群里一位校友父亲贴了一张求助贴,然后这贴飞速地在微信群转发,一位校友不幸全家中招,男主人气管插管。大家均为他们祈祷,愿全家早日康复,我相信他们在大家支持下,在医务团队努力下会康复的。
疫情面前谁都会恐慌,我也会恐慌。方方说过,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然而恐慌却是可以象病毒一样地快速传播的,这是人性的弱点。重要的是我们要从恐惧中超脱出来,树立必胜的信心,坚定必胜的勇气。正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所说,“勇气并不是不带有恐惧,只是我们还有比恐惧更重要的东西(courage is not the absence of fear, but rather the assessment that something els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fear.”)。又如丘吉尔曾说的,“ 除了恐惧本身外,没有别的可以恐惧的了(We have nothing to fear but fear itself)“。
既然如此,我更喜欢选择信心与勇气,让恐慌见鬼去吧。
新冠随笔链接:
美国抗新冠时期随笔(3)
美国抗新冠病毒时期随笔(2)
美国抗新冠时期随笔(1)
JAMA: 意大利与COVID-19相关的病死率和患者死亡特征
2020年2月上半月,意大利仅发现有3例2019年冠状病毒病-2019(COVID-19),所有3个病人近期都曾到过中国。2020年2月20日,在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地区(Lombardy),一名30多岁的男子被诊断出因SARS-CoV-2(严重的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冠状病毒-2)引起的严重肺炎病例,该男子没有在国外接触史。在14天之内,在周边地区诊断出许多COVID-19病例,其中包括大量危重病人。根据病例数和疾病的发展时期·可以推断该病毒从一月开始就一直在人群中传播着。
在与伦巴第接壤的威尼托(Veneto)同时发现了另一群COVID-19患者。此后,在意大利确诊的病例数迅速增加,主要是在意大利北部,但是该国所有地区都有COVID-19的患者报告。意大利目前仅次于中国,是第二大COVID-19病例集中地,并且病死率很高。本位3回顾了意大利在COVID-19方面的经历,重点是死亡人数。
监视系统和总死亡率
在COVID-19爆发初期,意大利国立卫生研究院(ISS)启动了一个监视系统,以收集全国所有COVID-19患者的信息。有关COVID-19病例的数据均来自意大利的所有19个地区以及特伦托和博岑两个自治省(Trento and Bozen)。通过逆转录酶-聚合酶链反应(RT-PCR)测试确诊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冠状病毒2(SARS-CoV-2)的COVID-19病例。病死率定义为SARS-CoV-2呈阳性检测的死亡人数除以SARS-CoV-2阳性病例数。根据截至3月17日的数据,意大利人群中已确诊COVID-19的人群的总死亡率为7.2%(1625例死亡/ 22,512例病例)。该比率高于其他国家/地区,原因可能与3个因素有关。
病死率和人口年龄
意大利人口特征与其他国家不同。2019年,约23%的意大利人口年龄在65岁以上。COVID-19对年龄较大的患者更具致命性,因此意大利的年龄分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意大利与其他国家相比更高的病死率。该表显示了意大利与中国的特定年龄段的死亡率。
意大利的总病死率(7.2%)大大高于中国(2.3%)。当按年龄组对数据进行分层时,意大利和中国的0-69岁年龄组的死亡率似乎非常相似,但是在70岁以上的人群中,尤其是在80岁以上的人群中,意大利的病死率较高。这种差异很难解释。这两个国家的病例分布有很大不同:年龄在70岁或以上的人占意大利病例的37.6%,而在中国仅占11.9%。另外,在意大利,相当多的病例发生在90岁以上的人群中(n = 687),该年龄段的病死率很高(22.7%);中国未报告90岁或90岁以上人群的数据。此外,世卫组织-中国冠状病毒病2019年死亡率联合特派团的报告提供了中国55 ,924个实验室确诊病例中2,114例与COVID-19相关的死亡数据,该报告报告了80岁或以上的患者中的病死率与意大利样本中的比率相似(中国为21.9%,意大利为20.2%)。
因此,意大利相对于中国的总体年龄分布可能部分解释了意大利较高的平均病死率。
与COVID-19相关的死亡的定义
对于意大利高病死率的第二种可能的解释可能是在意大利如何识别与COVID-19相关的死亡。意大利的病死率统计基于将COVID-19相关的死亡定义为通过RT-PCR测试SARS-CoV-2呈阳性的患者中发生的死亡,而与可能导致死亡的先前已有的疾病无关。选择此方法是因为目前尚无清晰的COVID-19相关死亡定义标准。
选择以这种方式定义死于COVID-19的死亡可能导致对病死率的高估。在意大利死亡的355例COVID-19患者的子样本详细数据显示在这些患者中,平均年龄为79.5岁(SD,8.1),其中女性为601(30.0%)。在该样本中,缺血性心脏病患者117例(30%),糖尿病患者126例(35.5%),活动性癌症患者72例(20.3%),房颤患者87例(24.5%),痴呆患者24例(6.8%), 34(9.6%)有中风病史。既往疾病的平均数量为2.7(标准差,1.6)。总体而言,只有3名患者(0.8%)没有疾病,有89名(25.1%)有一种疾病,有91名(25.6%)有2种疾病,有172名(48.5%)有3种或更多基础疾病。这些合并症的存在可能增加了独立于COVID-19感染的死亡风险。
到目前为止,现有国际报告中并未明确定义与COVID-19相关的死亡,对于与COVID-19相关的死亡定义,不同的定义可能解释了不同国家之间病死率的差异。为了更好地了解实际死亡原因,ISS正在审查在意大利死亡的所有RT-PCR结果均为阳性的患者的完整医疗记录。
测试策略
关于特定国家/地区病死率的差异的第三个可能解释是SARS-CoV-2 RT-PCR测试所使用的策略不同。在最初的广泛检测策略中,在流行病的非常早期阶段就对感染患者的症状和无症状接触进行了评估,意大利卫生部于2月25日发布了更严格的检测政策。该建议优先考虑对怀疑患有COVID-19且需要住院的更严重临床症状的患者进行检测。对于无症状的人或症状轻微的人,测试是有限的。这种测试策略产生了很高的阳性结果比例,即19.3%(阳性病例,截至2020年3月14日,在109, 170中已测试的21 ,157人),并且病死率显着增加,因为表现较少的患者不再对严重的临床疾病(因此死亡率较低)进行测试(病死率从2月24日的3.1%变为3月17日的7.2%)。这些病死率较低的较轻度病例因此不再计入分母中。
其他国家有不同的测试策略。例如,韩国采取了广泛测试SARS-CoV-2的策略。这可能导致鉴定出许多症状较轻或症状有限的个体,但与意大利相比病死率低得多(1.0%比7.2%),因为许多患有轻度疾病的患者在意大利就不计入分母(但韩国会计入分母)。
结论
总之,目前的数据表明,意大利确诊COVID-19感染的老年患者比例很高,而且意大利的老年人口可能部分解释了国家之间病例和病死率的差异。在意大利,COVID-19死亡主要发生在年龄较大的男性患者中,这些患者也有多种合并症。但是,这些数据是有限的,并且来自意大利记录的COVID-19病例的第一个月。此外,一些当前被感染的患者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死亡,这可能会改变病死率模式。
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测试政策的透明度是很必要的,并且在比较COVID-19病例时清楚地报告了用于计算病死率和受影响人群的年龄,性别和临床合并症的分母和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病死率。最后,由于是新的疫情,因此需要来自多个国家/地区的持续监控,以透明,准确的方式报告患者特征和检测政策,以更好地了解COVID-19的全球流行病学。
注:死亡率(mortality)指在一段时间内死亡人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而病死率(fatality)指在一段时间内死亡人数占所有病例数的比例。
眼泪传播新型冠状病毒的风险很低
新冠病毒正式名字是SARS-CoV-2, 由它引起的一类疾病叫做Covid-19(冠状病毒病-19),这类病包括可致命的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北美华人医师联盟告示
JAMA: 从围堵到缓解:美国的COVID-19
冠状病毒病2019(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是由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冠状病毒2(SARS-CoV-2)感染导致的呼吸系统疾病。在中国最初报告疾病暴发后,COVID-19已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至少遍及6大洲的67个国家。3月2日,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瑟姆(Gavin Newsom)宣布拨款2000万美元,并动员该州的应急管理系统来应对COVID-19。此外,171名在游轮中感染SARS-CoV-2患者在2月5日被疏散到加利福尼亚的美国空军基地。对这些无症状或仅有轻度症状的患者采用的是围堵策略(Containment)将他们转移到当地医院。当少数感染患者位于集中地点时,围堵策略(即隔离)可通过隔离感染来阻止感染传播。但是,要控制疾病,必须使用空气传播(airborne) 隔离室,个人防护设备和其它的一次性设备,以及大量的医护人员。目前由于COVID-19在美国和世界各地都在传播,因此不可能再以这种方式照顾所有患者。
在美国,出现了许多新的COVID-19阳性病例,这些病例缺乏清晰的旅行史或接触疑似病例信号,表明SARS-CoV-2的社区传播已经开始,并且正在医院的收容区域外发生。因为这些患者事先并非被确定为疑似病人,所以多个社区成员和卫生保健工作者可能暴露于SARS-CoV-2。结果,医院工作人员在进行症状发作和感染证据评估时被隔离检疫。这些事件不仅影响向怀疑和确诊的COVID-19病例提供病人护理的医院,而且还限制了附近的急诊室(ED),重症监护病房和住院病房的人员。至关重要的是,应采取措施遏制COVID-19大流行,必须改变策略:及从遏制(围堵, Containment))到缓解(Mitigation)。缓解方法旨在:(1)减慢病毒的进一步传播;(2)减少预期的医疗保健使用的激增;(3)为患者提供适当的护理水平,大多数患者只接受有限治疗的可能性。需要有时间限制的家庭隔离,(4)扩展测试功能以增加可用的医院容量,以及(5)调整隔离以最大程度地减少SARS-CoV-2的传播。如果在医院之间无法迅速采用这些方法,则COVID-19将对业已经紧张的医疗体系构成重大风险。
新的数据表明,SARS-CoV-2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基于R0为2.0至2.5,它比季节性流感更容易传播,并且可以通过无症状或症状轻微的人群传播,这些患者通常不会就医。感染SARS-CoV-2的患者中有80%表现出轻微或轻度的症状。结合这些特征和社区传播的出现,病毒很可能已经在美国多个地区进行了悄无声息的传播。结果,对COVID-19的围堵不再现实,进一步强调围堵策略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即妨碍了感染COVID-19的患者和其他需要常规医院护理的患者的有效医疗服务。在加州Kaiser Permanente,应急管理和准备团队根据良好的临床实践,现有证据和以往经验,制定了COVID-19缓解计划(表)。该计划是否将有效实现缓解尚不清楚。
表。
冠状病毒病拟议计划的关键要素(2019在北加州凯撒永久居民中的社区缓解措施)
在急性病护理环境中,重点应放在将疾病传播最小化上。由于SARS-CoV-2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因此防疫计划将会集中于确保使用可靠的飞沫预防措施。个人防护设备将包括手术口罩(surgical masks),一次性防护服,手套和防护眼镜的使用。这种方法旨在简化工作流程,并为诸如肺结核等疾病的患者保留使用增强的空气传播预防防护器材(如N95口罩)和受控或动力净化空气呼吸器。对于高风险的操作(包括气管插管和支气管镜检查),将继续采取全面的空气隔离预防措施。医院中的所有单间都可以做飞沫隔离,为需要真正的空气隔离的患者保留了数量有限的负压室。病人的运输,包括通过紧急医疗服务的运输,应同样采取飞沫传播预防措施。缓解COVID-19的要求还包括:无症状或仅具有轻度病毒性呼吸道感染症状的患者将被要求待在家里,直到他们症状好转(例如,发烧消退,咳嗽得到缓解)。建议有症状的家庭成员避免密切接触。基于临床或流行病学考虑,被隔离在家中的患者可能也会接受特定的SARS-CoV-2检测。与用于流感的疾病的方法类似,建议患者在症状缓解之前不要上班或上学。
如果患者的症状恶化,医护建议可以通过电话或视频会议和治疗协议进行远程护理,以确保在适当的情况下保持社会距离。对于具有进行性或更严重症状的患者,指定在特定的位置进行门诊评估,例如明确标识的门诊诊所位置,独立式结构(例如,帐篷)或移动测试装置,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对医护人员和其他人员的接触。患者将能够根据需要启动自行开车或基于紧急医疗服务的救护车到急诊室。必须为住院患者和门诊患者提供类似于当前的流感快速检测方案的SARS-CoV-2检测,以获取社区传播的程度,并确保在急诊室和医院单元中使用单间隔离。根据拟议的计划,将按照现有的防飞沫传播措施,对住院的有感染症状的患者在单间内进行护理。在受影响的住院病人数量激增的情况下,如果大家都知道SARS-CoV-2呈阳性,那么可能会将多名病人放在一个房间内。通过对医院容量的持续监控,动态评估将确定是否需要其他地点,例如流动医院单位。对患者就诊的限制与针对H1N1流感大流行的限制类似,在该限制中,有症状和不带家属的成员被要求避免去医院就诊。在家中症状缓解的患者可以像季节性流感一样重返工作或上学。基于医院的隔离将一直持续到出院或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发布的测试建议来决定。
即使医护人员休假政策在遏制阶段有效,但在社区不断蔓延的情况下,这些政策是无效的,在此期间,员工可能会像在医疗机构外一样容易受到感染。拟议的计划将遵循与暴露于流感的类似方案。工作场所接触怀疑或确诊为COVID-19的患者的人员应自我监控是否出现发烧,咳嗽和其他症状。如果他们生病并且被确认没有COVID-19,则工作人员将继续下班,直到发烧消退并且他们的其他症状开始好转为止。根据CDC指南,确认COVID-19的医疗保健人员应下班。
医疗保健防护产品供应商正在通知医院,COVID-19专用和其他常规用品的医疗用品可能会有数量限制。个人防护设备可能会受到严重限制,所以强调遵循与病毒传播机制保持可用性一致的隔离协议的重要性。私立医院系统与联邦,州和地方当局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将至关重要。COVID-19正在加利福尼亚州和美国其他地方进行社区传播,对卫生保健系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如拟议的计划中所建议,从遏制策略转变为缓解方法,可以在人员紧张的情况下优化卫生保健的提供,优化卫生保健系统中供应短缺。医院和州之间共享的明确指南可以帮助提高为所有患者可持续防控方法的能力。大流行带来很多不确定性,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公共卫生当局与医院系统合作的独创性对于改变策略以满足这种流行病的需求至关重要。
Article Information
March 13, 2020
From Containment to Mitigation of COVID-19 in the US
Corresponding Author: Stephen M. Parodi, MD, The Permanente Medical Group, Kaiser Permanente, 1950 Franklin St, Oakland, CA 94612 (stephen.m.parodi@kp.org).
Published Online: March 13, 2020. doi:10.1001/jama.2020.3882
Conflict of Interest Disclosures: None reported.
Funding/Support: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The Permanente Medical Group and grant R35GM128672 (awarded to Dr Liu) from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General Medical Sciences.
References
1.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situation summary. Accessed March 2, 2020.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summary.html
2. Wu Z, McGoogan JM. Characteristics of and important lessons from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outbreak in China. JAMA.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4, 2020. doi:10.1001/jama.2020.2648
3. Jernigan DB; CDC COVID-19 Response Team. Update: public health response to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outbreak—United States, February 24, 2020. MMWR Morb Mortal Wkly Rep. 2020;69(8):216-219. doi:10.15585/mmwr.mm6908e1
4. Hellewell J, Abbott S, Gimma A, et al. Feasibility of controlling COVID-19 outbreaks by isolation of cases and contacts. Lancet Glob Health. 2020;S2214-109X(20)30074-7.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8, 2020.
5. Bai Y, Yao L, Wei T, et al. Presumed asymptomatic carrier transmission of COVID-19. JAMA.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1, 2020. doi:10.1001/jama.2020.2565
给 Secretary Azar 及 Director Fauci 的信
对Covid-19轻症或疑似患者非公寓式居家隔离具体做法的建议
Covid-19居家隔离具体做法的建议
2. 房间内备有:床,口罩,体温计,有盖子的垃圾桶(最好脚踏式),充足的大小号垃圾袋,手机以及充电器;
4. 常备家庭医生诊所号码或者online Doctor App;以便随时与家庭医生保持联系。按照医生交待的,比如若出现发烧不退,高烧,呼吸局促等等要及时和家庭医生联系,按照指导安排下一步措施,比如去急诊等等;
5. 备好当地医院急诊科的地址,需要和家庭医生商量在万一需要去急诊科时是由家人送去还是叫救护车;
6. 被隔离人如果需要出房间,必须戴口罩。其他家人也要戴口罩并远离这个房间。送饭送到门口,不见面交接;
7. 被隔离人如果需要进出家门(比如去医院),尽量和其他家人走不同的门;
8. 房间垃圾单独存放,单独丢掉。单独洗衣服。衣物必须高热烘干;
9. 家中常备一次性手套,能杀死99.9%病原体的消毒液disinfectant,比如Lysol,Clorox等。家属在处理被隔离人用过的物品时(如垃圾袋,衣物,餐具等),应戴一次性手套,口罩,防护镜(或眼镜);处理完后立即洗手;
10. 家属每天用消毒巾擦门把手,电灯开关,常用台面,冰箱门把手,厕所flash 开关等常用的公共触摸区域。要注意更换消毒巾。不要用一块消毒巾擦多个表面;
12. 每天消毒厕所;
13. 保持平和冷静
马惠芳- My Favorite Dental Clinic. 508 Prudential Rd STE 300,
Horsham,PA,19044
新冠时期该如何正确地洗手?
1)用干净的自来水(冷或热水均可)打湿双手,关闭水龙头。
2)然后用肥皂。
3)用肥皂擦手使手起泡沫。
4)在手背,手指之间和指甲下搓起泡沫,擦洗双手至少20秒钟。需要计时器吗?从头到尾哼唱两次“生日快乐”歌曲就差不多了。
5)自来水下彻底冲洗双手。
6)用干净的毛巾、纸巾擦干双手或风干。
浅析CDC新冠指南在普通门诊的应用
新冠疫情在美国已经不可避免,目前有80例本土感染,死亡人数达9位(数字每天在变)。疫情在社区蔓延开的时候,门诊医生们往往处在抗疫的第一线。然而很多普通门诊都没有负压隔离病房。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医护人员,又能正确处理具有急性呼吸道症状和发热的病人呢?
首先,根据CDC指南正确地评估和分诊具有急性呼吸道症状的病人,降低医护人员感染病毒的机会。需要做好一个分诊的流程图,让前台接待员在病人电话或者是电脑预约的时候可以使用。询问所有预约病人的症状,如果有发热、咳嗽、呼吸困难这些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同时又有去疫区的旅行史或者跟确诊的新冠病人密切接触史,那么根据CDC的指南,他们是符合疑似新冠病人(PUI)的标准(见下表)。这时,需要立即给当地的卫生防疫部门或者是医院系统的传染病专家打电话,而他们会接手病人下一步的测试。病人暂时不要到诊所来,这样就减少了病毒感染整个诊所和医护人员的机会,从而进一步降低了医源性密集性传染社区的风险。
Contact your local or state health department
Healthcare providers should immediately notify their localexternal icon or stateexternal icon health department in the event of a PUI for COVID-19.
Criteria to Guide Evaluation of PUI for COVID-19
As availability of diagnostic testing for COVID-19 increases, clinicians will be able to access laboratory tests for diagnosing COVID-19 through clinical laboratories performing tests authorized by FDA under an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EUA). Clinicians will also be able to access laboratory testing through public health laboratories in their jurisdictions.
This expands testing to a wider group of symptomatic patients. Clinicians should use their judgment to determine if a patient has signs and symptoms compatible with COVID-19 and whether the patient should be tested. Decisions on which patients receive testing should be based on the local epidemiology of COVID-19, as well as the clinical course of illness. Most patients with confirmed COVID-19 have developed fever1 and/or symptoms of acute respiratory illness (e.g., cough, difficulty breathing). Clinicians are strongly encouraged to test for other causes of respiratory illness, including infections such as influenza.
Epidemiologic factors that may help guide decisions on whether to test include: any persons, including healthcare workers2, who have had close contact3 with a laboratory-confirmed4 COVID-19 patient within 14 days of symptom onset, or a history of travel from affected geographic areas5 (see below) within 14 days of symptom onset.
International Areas with Sustained (Ongoing) Transmission
Last updated February 28, 2020
-
China (Level 3 Travel Health Notice)
-
Iran (Level 3 Travel Health Notice)
-
Italy (Level 3 Travel Health Notice)
-
Japan (Level 2 Travel Health Notice)
-
South Korea (Level 3 Travel Health Notice)
-
其次,根据CD C的感染防控指南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PC),制定修改符合自己诊所的感染防控规章制度。因为有的病人不通过预约会直接到诊所来,另外根据CD C的指南,还有一类病人就是有急性呼吸道症状,但是没有旅行史或接触史,如果能够排除其他原因引起的症状,也符合上面所说的疑似新冠病人标准。这一部分病人就必须到诊所里来,才能排除其他原因。而这个过程就存在着污染整个诊所的可能性。在此之前,制定好整个诊所的感染防控规章制度,培训好诊所的所有员工就至关重要。这包括1. 照顾病人时的标准防护、接触防护、空气飞沫和眼睛的防护。2. 看病人之前和之后,接触到有可能污染物质之后,穿上个人防护用具之前和脱掉防护用具之后正确的洗手程序。3. 学习和训练如何正确地穿脱个人防护用具,以降低自身污染的可能性。4. 在可能产生气雾的操作过程中,正确使用个人防护用具和遵循正确的操作规范。
第三就是注意环境的清洁与消毒。常规的消毒和清洁诊所对新冠病毒的防控也是合适的,包括产生气雾操作过程中病人所在的区域。正确处理衣物,食品用具,医源性废物。
最后, 还要知道何时联系当地卫生防疫部门和职业健康机构。当医护人员在没有防护状态下接触到疑似或确诊的新冠病人,应该立即向职业健康部门汇报。如果医护人员出现了疑似新冠症状,如发烧,咳嗽,呼吸困难等,留在家里不要上班,并马上联系职业健康部门。
reference: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hcp/caring-for-patients.html
JAMA:医用口罩是可用于预防呼吸道感染传播的工具。
什么时候应该使用口罩?
只有具有呼吸道感染症状的人才可以使用口罩,例如咳嗽,打喷嚏或在某些情况下发烧的病人。
医护人员,正在照料或与呼吸道感染患者密切接触的人,或者在医生认为应佩戴情况下,也应戴口罩。
健康的人不应戴口罩(以保护自己免受呼吸道感染),因为没有证据表明健康的人戴口罩可以有效地预防人患病。
口罩应留给有需要的人使用,因为在广泛的呼吸道感染期间口罩可能供不应求。由于N95呼吸防护口罩需要进行特殊的贴合测试,因此不建议公众使用。
如何戴口罩?
如果确实要戴口罩,在戴上口罩之前,请先用肥皂和水洗手至少20秒钟,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没有肥皂和水,也可以使用酒精含量至少为60%的酒精消毒剂。
清洁双手后,将面罩放在鼻子和嘴巴上。确保面罩和您的脸之间没有缝隙,并确保紧密密封。戴上口罩后请尽量避免用手接触口罩。如果您确实触摸了面罩,请洗手或再次使用洗手液。使用完口罩后,请在不接触口罩正面的情况下将其卸下,然后将其丢弃在密闭的容器中。丢弃口罩后,再次洗手。
预防感染
手的卫生是防止获得和传播呼吸道感染的最重要方法之一。经常洗手。洗手之前,请勿触摸鼻子,眼睛或嘴巴。避免与其他患病的人密切接触。如果有的话,用清洁布或清洁喷雾清洁家庭表面和物体。如果生病,请留在家中,以免传染给其他人生病。
附英文:
When Should a Mask Be Used?
-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about/prevention-treatment.html
Article Information
基于CDC关于流感预防经验,进一步提高医院内感染控制
金冲飞/ANACP
参考来源
武汉疫情上报第一人——张继先医生讲座纪要
12月29日张继先医生将4个华南海鲜市场的人员病患再次上报。
张医生回答了微信提出的问题。
3)没有症状但是核酸没转阴怎么处理?
14)通过正规途径上报的医生出了您,知道还有谁吗?
最近要出国旅行吗?美国CDC旅行指南更新
同济医院感染病科陈韬教授讲座总结
一)抗新冠总体和临床表现:
同济医院抗新冠简介(统计,诊疗原则,流程,发病趋势)
12月底,武汉市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同济医院即做出应对措施,第一时间成立发热门诊(日就诊量约70人次),由呼吸科、感染科、急诊科人员组成,并成立由这三个科室人员组成的专家组,指导在院和发热门诊疑似病人的甄别工作。随着疫情的快速进展,医院不间断扩张发热门诊留观病房,但是仍然不能满足就医需求,于1月11号(日就诊量约300人次)建立发热病房,由1个病区迅速增加到3个病区,收治约50名重症患者,由呼吸科、感染科各2名高年资教授带组,医院从全院非手术科室、手术科室抽调医师组建。从1月中旬到1月底,病人呈爆发式增长,武汉市成立多个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医院,1月29日汉口主院区的发热门诊的日门诊量达到1000人次,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成为重症患者定点收治医院,。第一期550张床位逐步开放,5天全部收满,2月7号开放第二期550张床位,3天全部收满,这个期间来自北京、吉林、湖南、山西的医疗队逐步进驻中法院区。2月15日,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成为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医院,600张床位全部收满。期间中央政府加强对湖北省防控指导,从封闭武汉市外出通达、封闭三镇公共交通、封闭社区这些阻断传播途径的举措,加强对疑似病例的筛查,成立方舱医院,目前发病人数基本稳定,估计到3月初会呈现下降趋势。
疫情初始,医务人员对于新冠肺炎的诊疗均不熟悉,我院由我们感染科宁琴教授牵头,组织呼吸科、急诊科专家,结合我们自己的诊治经验撰写《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快速推荐建议》一共历经4版,我是执笔人,最近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对于湖北省地市医院的防治发挥了指导作用,其中我们自己的经验,也被卫健委的指南采纳。
二)死亡病例, 为什么武汉的死亡率大大于外地?
对于武汉COVID-19患者是不是武汉相对医疗需要显得为医疗体系如此薄弱(比如医疗防护设备缺乏,医疗资源短缺,交叉科室医护的应用,及病人太多而导致的病死率更高?还是武汉的医疗体系本身就有些薄弱而导致?还是有其它的原因呢?武汉COVID-19患者的死亡率是比中国其它地方要高吗?
三)诊断:
四)治疗:
五)预后:
六)经验:
美国临床医生为新冠疫情做准备的清单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已开通电邮通知系统,建议朋友们注册一下,以关注病毒发展及防御最新信息,注册程序很简单,只需输入你的电子邮箱地址。如愿注册,请打开这个链接,在最下面填入你的电子邮箱地址即可。希望大家平安渡过这个波及多个国家的病毒疫情。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php/preparing-communities.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我从中国来,我需要做个胸片买安心么?”
家庭护理新冠病人(COVID-19)及相关事项
CDC昨天2/21/2020发出COVID-19全国流行可能的警告,并着手防备工作。
这里讨论新冠或疑似新冠病人的家庭护理问题。
对于不需要住院的新冠病毒感染的病人,医务工作者应该与当地的卫生部门联系,决定病人是不是应该在家隔离。
1.首先决定病人的情况是不是稳定。
2.家里有没有人照顾。
3.有没有独立的房间可以与其他人隔离。
4.食物与其他的生活用品是否容易获得。
5.病人与照顾者有没有个人防护用品,至少有没有手套和口罩,并能够遵循隔离的原 则。
6.家里有没有高危人群,如果65岁以上老人,小孩,孕妇,免疫低下者,或者有慢性心 肺肾脏的疾病者。
对于新冠病毒感染患者或疑似已受感染者,请遵循以下步骤,以防止将新冠病毒传播给其他人。
请隔离在家,呆在自己的房间,与家里其他人及宠物隔离。
若要去医院就诊,请不要用公共交通或者叫出租车,请提前告诉诊所或医院你已经患了或者怀疑患了新冠病毒感染。
出门的时候,或者与任何人接触的时候请带口罩。
咳嗽或者打喷嚏的时候,请用纸巾遮盖嘴和鼻子,然后丢掉纸巾,马上用肥皂和水清洗双手至少20秒钟,或者用酒精类的清洁液清洁整个手部。
平时经常洗手,家里人不要合用任何东西。
每天清洁常常接触的表面,如桌面,手把,键盘,厕所,手机等等。
如果您的症状加重,请尽快与您的医生联系,就诊前请务必打电话说明情况。
如果有紧急情况,请打911,并且在电话上告知你的情况。
请遵循医生与医务部门的指导,以决定什么时候可以解除隔离。
解除隔离和出院后注意事项
解除隔离标准需满足以下4个条件:
1.体温恢复正常3天以上;
2.呼吸道症状明显好转;
3.肺部影像学显示急性渗出性病变明显吸收好转;
4.连续两次呼吸道标本核酸检测阴性(采样时间至少间隔1天)。
出院后注意事项
1.定点医院要做好与患者居住地基层医疗机构间的联系,共享病历资料,及时将出院患者信息推送至患者辖区或居住地居委会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2.患者出院后,因恢复期机体免疫功能低下,有感染其它病原体风险,建议应继续 进行14天自我健康状况监测,佩戴口罩,有条件的居住在通风良好的单人房间,减少与家人的近距离密切接触,分餐饮食,做好手卫生,避免外出活动。
3.建议在出院后第2周、第4周到医院随访、复诊。
有问题可查询 www.cdc/COVID19
新冠疾病(COVID-19)的风险评估
by 静心无尘
高危人群
1.从中国湖北省回来
2.有与新冠病人接触史,如一起生活或者直接在家照顾新冠病人,自己没有严格遵循保护措施。
无症状者,在家隔离有症状者,就医隔离。
中危人群
1.有与新冠病人接触史,如一起生活或者直接在家照顾新冠病人,自己严格遵循保护措施。
2.与病人在6尺(feet)内长时间的接触史;或者接触了新冠病人的呼吸道分泌物。
3.从中国回来者.
无症状者,在家隔离有症状者,就医隔离。
低危人群
与新冠病人在同一个室内空间,如同一个教室或者同一个医院候诊室等。
无症状者,自我隔离14天后可以恢复正常生活。没有建议胸部X光检查。
以下为CDC的评估流程指南 2/14/2020.

冠状病毒阅读:生物学、致病性和疫苗研发
说说口罩
医用口罩有很多种,最近在国内风靡的N95其实医院里不是很常用。鉴于现在疫情的原因,我把N95列在我分类的第一位。医用口罩一般分三类:
从CDC的抗新冠反应看美国的防疫系统
此刻我们北美华人医师联盟比您更激动
ANACP抗新冠病毒募捐活动更新
(第一批经过绿色通道物资:1.7万个N95口罩送达武汉及周边医院!)
编辑:风城黑鹰
|
|
|
|
|
|
|
|
|
|
|
|
|
|
|
湖北省鄂州中心医院的货物:
谁动了我的口罩
Zhf
北美华医联盟捐赠工作小结(2/7/2020)
1. 联盟目前为止已经收到捐款总额89940.01美元,捐款人次 579。
2. 已经购买物资:N95 医用口罩 24000个,外科和护理口罩 合计60000余个,护目镜4000个。
3.第一批大量物资:N95医用口罩17000个,已经到达武汉,陆续配送到武汉及周边10家医院。
4. 第二批大量物资:近7000 个N95医用口罩,近60000个外科和护理口罩,2000个护目镜已经准备就绪,将于下周一通过不同渠道运往武汉,温州,上海,湖南,广东等35家医院。
5. 联盟已经关闭为新冠病毒捐款通道,并继续将所余款项用于购买物资和运输以支援一线医护人员。所有工作完成以后,会向大家汇报捐款总额,物资总额,以及物资定点医院。
6. 我们已经逐渐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北美冠状病毒的传播情况,医学科普,学术交流探讨等方面。
7. 非常感谢所有会员,非会员捐款人的大力支持。
8. 联盟对李文亮医生的去世表示深切悲痛,向他的家人朋友表示诚挚的慰问和关切。我们会密切关注相关可靠信息,讨论合理有效的方法以尽我们的微薄之力帮助他的家人。
ANACP

恩施市主管防疫物资的副市长(左三)向华医联盟的捐献表示感谢。恩施市共收到口罩60万余,但N95口罩只有1010只,全部来源于华医联盟捐献。

北美华人医师联盟沉痛悼念李文亮医生
明旭记
Zhf
庚子年冬,冠毒肆掠,神州告急。烽烟四起,群雄辈出。有北美华医联盟者,虽远于海外,亦欲援之。惊闻铠甲护具奇缺,则捐金集物,广收细查。有探者报, 货之所在,塞北奇寒之地。何以得之?
一员儒将越众而出,某愿一试。此乃辽东名将,徐生,明旭也。遂千里单骑,风餐陋宿,星夜疾驰,押货而返。
联盟因其勤勉,授转运使。一应护甲辎重,皆汇徐家大营,辗转神州。明旭莫敢懈怠,日夜巡营,物归其类,数入其库。复查栈道消息,避险滩匪类。个中扑簌迷离,瞬息万变,不足为外人道也。纵百般艰难,亦千山飞度。
不日,毒侵北美。明旭日防冠毒,夜行转运。妻子弟兄皆现阵前。故友至,视徐家军白衣软袍,愧之:君握8万护具,无半分于己身。遂发文书邻寨,暂借护具十余,方解明旭之困。
良将如斯,联盟之幸。特以此记。

我们戴上了口罩
风城黑鹰
北美华医联盟捐赠工作小结(1/31/2020)
1. 联盟目前为止已经收到捐款 $82501.86,捐款人次为539。
2. 已经购买物资:N95 医用口罩 24000个,surgical mask 和procedure mask 合计60000个,护目镜4800个,防护服750套,防护面罩5000个。
3.已经运出物资:N95医用口罩21000。通过不同渠道运往武汉以及周边省市14家医院。特别感谢武汉大学校友会提供绿色通道。
4. 本次联盟所捐赠口罩90%来源于北美非盈利组织的仓库. 他们的使命是收集医疗设备,运送到世界各地最需要的地方。在这次活动中与联盟进行了完美的合作。
5. 联盟将在2/1日关闭为新冠病毒捐款通道,并继续将所余款项用于购买物资和运输以支援一线医护人员。所有工作完成以后,会向大家汇报捐款总额,物资总额,以及物资定点医院。
6. 我们会逐渐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北美冠状病毒的传播情况,医学科普,学术交流探讨等方面。
7. 非常感谢所有会员医生,非会员医生,和广大非医生团体和个人的支持。
8. 特别感谢段蕾女士和她的先生吉力吉利帮我们联系非盈利组织,提供货源。
远水与近火--- 北美华人医师联盟援助武汉疫情纪实
2020年1月22日,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武汉封城。在北美华人医师联盟(ANACP)的会员群里,周医生问:我们可以为前线的医护人员做点什么?联盟董事会紧急讨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议。马上成立了由董事会和公益组成员构成的武汉疫情捐赠小组。鉴于国内医疗防护物品紧张,我们决定在北美购买物资,运送回中国,送到一线医护人员手中。N95医用口罩由于防毒最有效,又奇缺,而且体积小分量轻, 便于长途运输,成为联盟的首选。分管订货的徐严两位医生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寻找货源。这时网上已经开始缺货。他们扩展思维,跟当地的医疗设备公司订购了4000只口罩。下午,联盟在会员群公告,发动
会员捐款,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1月23日,联盟的武汉疫情基金已经收到一万余美金汇款。董事会立即决定追加8000只口罩的订单。同时联盟会员黄医生提醒我们,也应该做医学科普教育,帮助在美国的华人正确防护这种新型病毒。3小时以后“北美华人医师联盟友情告示”发表在美国医人公众号,目前已经超过4万阅读量,很好地起到了公益科普,预防
教育的作用。会员郭医生,金医生,汪医生也陆续发表公众号科普文章介绍这种新型病毒和肺炎;会员伍医生,董医生参加了程医生组织的武汉疫情远程心里咨询活动;会员张医生,杜医生,谢医生接受当地媒体采访, 呼吁民众的重视与预防;会员连医生,郭医生等纷纷提醒当地学校,华人组织关于这种肺炎的严重性
和传染性,直接促进了几大城市华人春节联欢活动的取消,减少了该病毒在美国华人群体中扩散的可能性。我们可以骄傲地说在援助武汉的同时,联盟医生们也守住了自己的阵地。
1月24日,除夕。这是先抑后扬的一天。一大早就收到医疗设备公司发的消息,我们两天前订购的口罩 "backorder"。我们惊呆了,没想到美国也有不讲信用的公司,订货时明明有的。然而,我们没有时间沮丧,立即开始重新寻找货源订货,并且发动会员们提供消息。其中,曹医生为我们带来了贵人, 她的师妹段蕾和先生吉力吉利。她们为联盟联系介绍了非营利组织:Partners for World Health。这个机构可以提供一万多只符合Noish 标准的N95医用口罩,对于我们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唯一困难是需要我们自己去缅因州提货。纽约的徐医生,毅然决定开车往返12 个小时,亲自提货,不惜关闭周一自己的诊所。同时, 我们已经收到会员Vivien 和严静茵直接捐赠的两箱医用N95口罩,一箱已经从休斯顿寄出,另一箱周六从纽约寄出 (武汉同济,协和两医院)。我们的财长汇报,捐款已达两万余元。除夕夜,董事会成员的新年愿望是:一觉醒来,房间里堆满口罩,然后口罩自己长翅膀飞向武汉......
1月25日,初一。联盟工作组成员却比平时更加忙碌,19名成员分工协作,忙而不乱。由于货源紧张,我们决定物资品种从N95医用口罩扩展到护目镜和防护服。货源小组的杨,涂两位医生连续几个小时在网上寻找,同时积极通过可靠渠道与国内医生沟通,确认正确的型号。订货小组徐,周,严三位医生根据她们的信息再仔细筛选,果断下单。陈医生一丝不苟地记录订货清单,度假期间也没有间断。负责运输和通关的陆药师,周医生积极寻找国际运输,海关清关,武汉入城的各种渠道。春媚医生推荐的刘先生,有一家中美贸易公司,决定帮助我们搞定运输清关地面运输全套环节。居民联盟的Angela 也帮我们介绍了阿里物流。搜集记录医院联系人的曹医生,汪医生,刘医生,反复核实,及时更新急需物资医院的消息。财长周医生既要管记账又要帮忙订货,管网站的杨医生和严医生根据反馈,及时改进网站,方便捐款人,同时刊登联盟的科普公告。李医生帮助我们更新文学城账号,詹,王,陈三名医生负责监督提醒。新年第一天,联盟捐款总额超过五万,订货总额达八万多元(其中有些货物 back order)。董事会特批,差额由联盟基金预付。春媚医生组建了医学咨询-支援武汉小组,汇总了权威机构发布的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学术文章公大家学习交流,并积极组织相关讲座帮助临床医生更好地照顾病人。
1月26日,初二,应该是令人振奋的一天。各地医疗援助组赶赴武汉,海关的援助物资也陆续清关。华医联盟与同济海外校友会邀请了武汉著名医院之一的重症监护室主任为北美华人医生们做了一场精彩的讲座 ,从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性,典型与非典型症状,防治方法进行了系统的讲解,并且阐述了正确切断传播途径的方法。对于北美华人医生的临床工作,科普教育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同时,联盟的徐医生租了一辆卡车,抓了自己儿子做壮丁,从纽约出发,驱车6 个小时赶往缅因提取我们目前为止最大量的一批现货:一万多只符合Noish 标准的N95医用口罩。随着货源越来越近,联盟董事会必须对于运输渠道做出选择。鉴于小批量个人赠品经Fedex/USPS有在封城后到达武汉的先例,我们起初决定这第一批至关重要的物资化整为零,避开大批物资的清关手续,直接快递到一线医护人员手中。虽然运费高昂,但是金钱就是时间,时间就是生命。
正在心疼这估价过万美金的运费时候,武大校友,华医联盟的曹医生为我们联系到了武大校友会的绿色通道。他们非常感激我们的物资有一部分正是运往武大附属中南,人民, 和校医院的,愿意免费做我们的承运人,并且帮助我们将其余物资也运送到其他定点医院,并承诺5天左右到达,速度上与美国的快递齐平。于是,根据他们的清关和派送要求,我们立即制作货物标签,包括规格,数量,捐赠机构,提取人,定点单位联系人,中英对照,反复核对。同时,徐医生也在缅因当地华人的帮助下顺利装车,并且发回了令人欢欣鼓舞的照片。
这一天,两位汪医生还分别接受了路透社记者的电话采访。
1月27日,初三。今天下午,北美华人医师联盟捐赠的1万6千只符合Noish 标准的N95医用口罩经过徐医生的货车运达纽约。晚上,在武大校友会提供的绿色通道中飞向武汉,预计5天内配送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武汉大学校医院, 武汉市第三医院,武汉市第五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湖北省黄梅县人民医院,湖北恩施市中心医院,湖北鄂州市中心医院,湖北省大梧县人民医院的一线医护人员手中。另有3000 多只N95医用口罩即将到货。
迄今为止,联盟接受捐款近七万,离联盟已支付的八万差距在缩小,而我坐在电脑前写这篇记录。短短五天发生了无数感人的小故事,比如武汉医生发的信息“我还在,我的城我来守”,比如刚下夜班的住院医在凌晨给工作组成员打来电话,愿意提供运输渠道,比如工作组成员有的每天只吃一顿饭,睡两三个小时。不一而
足,无法一一详述。不仅想起两个成语“杯水车薪”和“远水近火“,本意是用来形容人类愚不可及的行为。然而,在过去几天里,北美华人医师联盟的医生们正在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做着这样”愚蠢“的行动。如果你也想像我们一样为武汉的疫情尽一点绵薄之力,欢迎按照以下信息捐款支持我们。

CDC:更新去中国旅游指南, 红色三级警告
On January 27, 2020 CDC issued updated travel guidance for China, recommending that travelers avoid all nonessential travel to all of the country (Level 3 Travel Health Notice).
1/27/2020 CDC:更新去中国旅游指南,红色三级警告,尽量不要去中国旅游
CDC Recommends
While the immediate risk of this new virus to the American public is believed to be low at this time, everyone can do their part to help us respond to this emerging public health threat:
目前该病毒对美国的公众危害尚低,
- For everyone: It’s currently flu and respiratory disease season and CDC recommends getting vaccinated, taking everyday preventive actions to stop the spread of germs, and taking flu antivirals if prescribed.
- 对所有人,目前是感冒与上呼吁吸道感染季节,
建议打感冒针及做法好预防措施 - For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 Be on the look-out for people with travel history to China and fever and respiratory symptoms.
- If you are a healthcare professional caring a 2109-nCoV patient, please take care of yourself and follow recommended infection control procedures.
- 对医务人员,要关注呼吸道病人的旅游史。
自己生病,要严格遵循CDC的建议。
- For people who may have 2019-nCoV infection: Please follow CDC guidance on how to reduce the risk of spreading your illness to others.
- 对可能感染的病人,打电话遵从家庭医生的指导。
- For travelers: Stay up to date with CDC’s travel health notices related to this outbreak.
- 对旅游者,随时查询CDC。
Dear friends,
The outbreak of a lethal coronavirus infection (2019-nCoV) in Wuhan, China has spread to different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Given the fact that large volume of Chinese traveled back to the USA during holidays, we must keep vigilant to ensure the safety within our community.
1. Early diagnosis and isolation is extremely important. If you have fever, cough or runny nose, please wear masks and quarantine yourself.
2. If the patient came from China within past month, especially from Wuhan City, please contact his/her primary care physician or the local Department of Health. They will give you further instructions. Try not to visit doctor office directly and avoid possible spreading of this highly contagious virus.
3. If patient is so sick and needs ER visit, please call ER first and report the exposure history before patient arrives.
4. Please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from CDC website.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about/prevention.html
5. Please avoid parties if you just came back from Wuhan, even if you have no symptoms, because the incubation period is 2 weeks.
Please follow the guidelines and help the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 Take care and God bless our community.